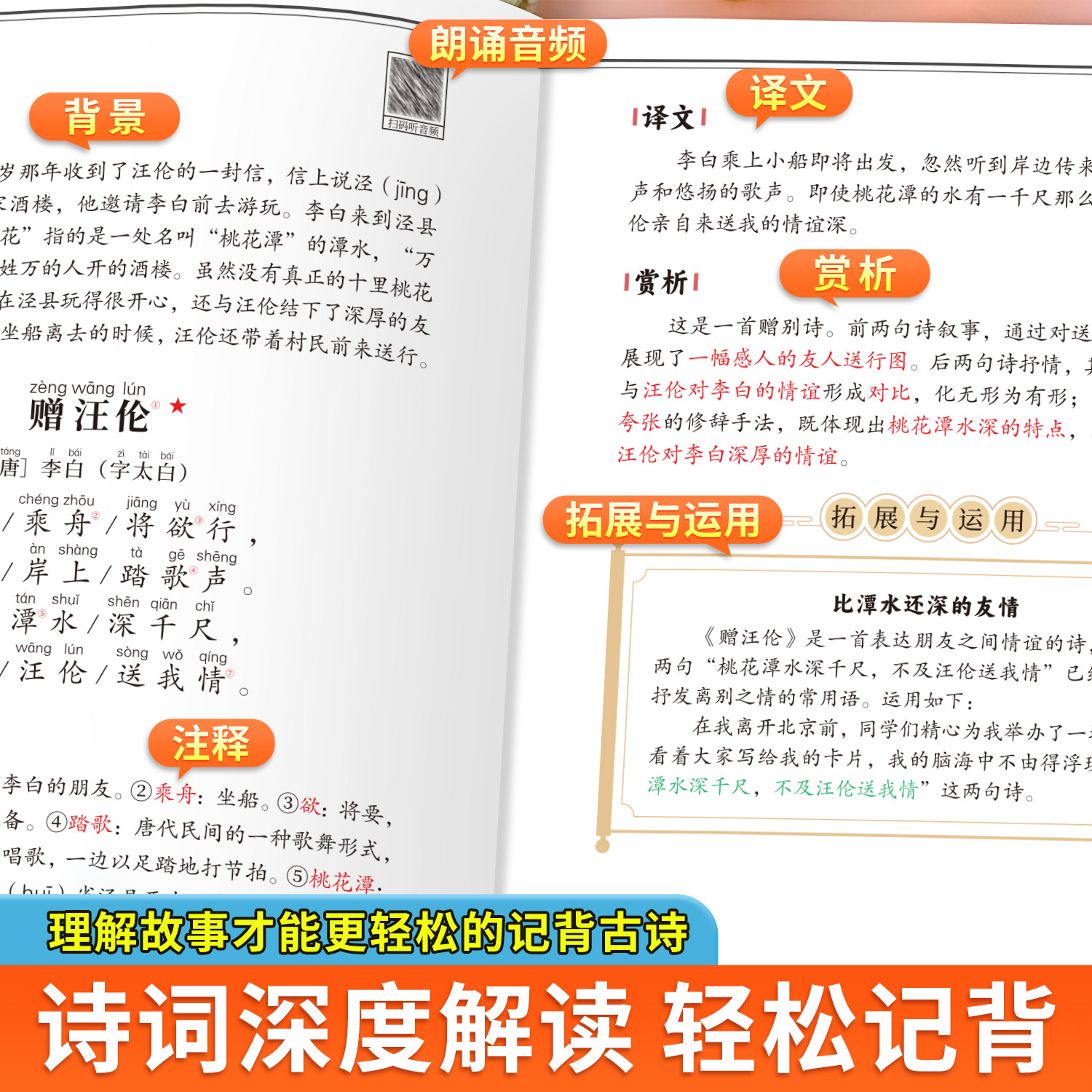卻說宋廷馳詔入關,召還柳元景以下諸將,詔中大略,無非因王玄謨敗還,柳元景等不宜獨進,所以叫他東歸。元景不便違詔,只好收軍退回,令薛安都斷後,徐歸襄陽。爲這一退,遂令魏兵專力南下,又害得宋室良將,戰死一人。 原來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,曾遣參軍胡盛之出汝南,梁坦出上蔡,攻奪長社,再遣司馬劉康祖,進逼虎牢。魏永昌王拓跋仁,探得懸瓠空虛,一鼓攻入,又進陷項城。適宋廷召還各軍,各歸原鎮,劉康祖與胡盛之,引兵偕歸。行至威武鎮,那後面的魏兵,卻是漫山遍野,蜂擁而來。胡盛之急語康祖道:“追兵甚衆,望去不下數萬騎,我兵只有八千人,衆寡不敵,看來只好依山逐險,間道南行,方不致爲虜所乘哩。”康祖勃然道:“臨河求敵,未得出戰,今得他自來送死,正當與他對壘,殺他一個下馬威,免令深入,奈何未戰先怯呢?”勇有餘而智不足。遂結車爲營,向北待着,且下令軍中道:“觀望不前,便當斬首!驚顧卻步,便當斬足!”軍士卻也齊聲應令。聲尚未絕,魏軍已經殺到,四面兜集,圍住宋營。宋軍拚命死鬥,自朝至暮,殺斃魏兵萬餘人,流血沒踝,康祖身被數創,意氣自若,仍然麾衆力戰。會日暮風急,虜帥拓跋仁,令騎兵下馬負草,縱火焚康祖車營,康祖隨缺隨補,親自指揮,不防一箭飛來,穿透項頸,血流不止,頓時暈倒馬下,氣絕身亡。餘衆不能再戰,由胡盛之突圍出走,帶着殘兵數百騎,奔回壽陽,八千人傷亡大半。 魏兵乘勢蹂躪威武,威武鎮將王羅漢,手下只三百人,怎禁得虜騎數萬,把他困住,一時衝突不出,被他擒去。魏使三郎將鎖住羅漢,在旁看守,羅漢伺至夜半,覷着三郎將睡臥,扭斷鐵練,踅至三郎將身旁,竊得佩刀,梟他首級,抱鎖出營,一溜風似的跑到盱眙,幸得保全性命。 拓跋仁進逼壽陽,南平王鑠登陴固守。魏主拓跋燾把豫州軍事,悉委永昌王仁,自率精騎趨徐州,直抵蕭城。前寫宋師出發,何等勢盛,此時乃反客爲主,可見勝敗無常,令人心悸。蕭城距彭城只十餘里。彭城兵多糧少,江夏王義恭,恐不可守,即欲棄城南歸。沈慶之謂歷城多糧,擬奉二王及妃女,直趨歷城,留護軍蕭思話居守。長史何勳,與慶之異議。欲東奔鬱洲,由海道繞歸建康。獨沛郡太守張暢,聞二議齟齬不決,即入白義恭道:“歷城、鬱洲,萬不可往,亦萬不易往,試想城中乏食,百姓統有去志,但因關城嚴閉,欲去無從,若主帥一走,大衆俱潰,虜衆從後追來,難道尚能到歷城、鬱洲麼?今兵糧雖少,總還可支持旬月,哪有捨安就危,自尋死路?若二議必行,下官願先濺頸血,污公馬蹄。”道言甫畢,武陵王駿亦入語道:“叔父統制全師,欲去欲留,非道民所敢幹預;道民系駿小字。惟道民本此城守吏,今若委鎮出奔,尚有何面目歸事朝廷?城存與存,城亡與亡,道民願依張太守言,效死勿去!”十一年南朝天子,是從此語得來。義恭乃止。 魏主燾到了彭城,就戲馬臺上,疊氈爲屋,瞭望城中,見守兵行列整齊,器械精利,倒也不敢急攻。便遣尚書李孝伯至南門,饋義恭貂裘一襲,餉駿橐駝及騾各數頭,且傳語道:“魏主致意安北將軍,可暫出相見,我不過到此巡閱,無意攻城,何必勞苦將士,如此嚴守!”武陵王駿,曾受安北將軍職銜,恐魏主不懷好意,因遣張暢開門報使,與孝伯晤談道:“安北將軍武陵王,甚欲進見魏主,但人臣無外交,彼此相同,守備乃城主本務,何用多疑?” 孝伯返報魏主,魏主求酒及橘蔗,並借博具,由駿一一照給,魏主又餉氈及胡豉與九種鹽,乞假樂器。義恭仍遣張暢出答。暢一出城,城中守將,見魏尚書李孝伯,控騎前來,便拽起吊橋,闔住城門。孝伯復與暢接談,暢即傳命道:“我太尉江夏王,受任戎行,末齎樂具,因此妨命!”孝伯道:“這也沒甚關係,但君一出城,何故即閉門絕橋?”暢不待說畢,即接口道:“二王因魏主初到,營壘未立,將士多勞,城內有十萬精甲,恐挾怒出城,輕相陵踐,所以閉門阻止,不使輕戰。待魏主休息士馬,各下戰書,然後指定戰場,一決勝負。”頗有晉欒鍼整暇氣象。孝伯正要答詞,忽又由魏主遣人馳至,與暢相語道:“致意太尉安北,何不遣人來至我營,就使言不盡情,也好見我大小,知我老少,觀我爲人,究竟如何?若諸佐皆不可遣,亦可使僮幹前來。”暢又答道:“魏主形狀才力,久已聞知,李尚書親自銜命,彼此已可盡言,故不復遣使了。”孝伯接入道:“王玄謨乃是庸才,南國何故誤用,以致奔敗?我軍入境七百里,主人竟不能一矢相遺,我想這偌大彭城,亦未必果能長守哩!”暢駁說道:“玄謨南土偏將,不過用作前驅,並非倚爲心膂,只因大軍未至,河冰適合,玄謨乘夜還軍,入商要計,部兵不察,稍稍亂行,有甚麼大損呢?若魏軍入境七百里,無人相拒,這由我太尉神算,鎮軍祕謀,用兵有機,不便輕告。”虧他自圓其說。孝伯又易一詞道:“魏主原無意圍城,當率衆軍直趨瓜步,若一路順手,彭城何煩再攻?萬一不捷,這城亦非我所需,我當南飲江湖,聊解口渴呢!”暢微笑道:“去留悉聽彼便,不過北馬飲江,恐犯天忌;若果有此,可是沒有天道了!”這語說出,頓令孝伯出了一驚。看官道爲何故?從前有一童謠雲:“虜馬飲江水,佛狸死卯年。”是年正歲次辛卯,孝伯亦聞此語,所以驚心。便語暢告別道:“君深自愛,相去數武,恨不握手!”暢接說道:“李尚書保重,他日中原蕩定,尚書原是漢人,來還我朝,相聚有日哩!”遂一揖而散。好算一位專對才。 次日,魏主督兵攻城,城上矢石雨下,擊傷魏兵多人。魏主遂移兵南下,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,高涼王拓跋那出山陽,永昌王拓跋仁出橫江,所過城邑,無不殘破。江淮大震,建康戒嚴,宋主亟授臧質爲輔國將軍,使統萬人救彭城。行至盱眙,聞魏兵已越淮南來,亟令偏將臧澄之、毛熙祚等,分屯東山及前浦,自在城南下營。哪知臧、毛兩壘,相繼敗沒,魏燕王拓跋譚,驅兵直進,來逼質營。質軍驚散,只剩得七百人,隨質奔盱眙城,所有輜重器械,悉數棄去。 盱眙太守沈璞,蒞任未久,卻繕城浚隍,儲財積穀,以及刀矛矢石,無不具備。當時僚屬猶疑他多事,及魏軍憑城,又勸璞奔還建康。璞奮然道:“我前此籌備守具,正爲今日,若虜衆遠來,視我城小,不願來攻,也無庸多勞了。倘他肉薄攻城,正是我報國時候,也是諸君立功封侯的機會哩!諸君亦嘗聞昆陽、合肥遺事麼?新莽、苻秦,擁衆數十萬,乃爲昆陽、合肥所摧,一敗塗地,幾曾見有數十萬衆,頓兵小城下,能長此不敗麼?”僚佐聞言,方有固志。 璞招得二千精兵,閉城待敵。至臧質叩關,僚屬又勸璞勿納,璞又嘆道:“同舟共濟,胡越一心,況兵衆容易卻虜,奈何勿納臧將軍!”遂開城迎質。質既入城,見城中守備豐饒,喜出望外,即與璞誓同堅守,衆皆踊躍呼萬歲。 那魏兵不帶資糧,專靠着沿途打劫,充作軍需。及渡淮南行,民多竄匿,途次無從抄掠,累得人困馬乏,時患饑荒,聞盱眙具有積粟,巴不得一舉入城,飽載而歸。偏偏攻城不拔,轉令魏主無法可施,因留數千人駐紮盱眙,自率大衆南下。 行抵瓜步,毀民廬舍,取材爲筏,屋料不足,濟以竹葦。揚言將渡江深入,急得建康城內,上下震驚。宋主亟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,率兵分扼津要,自採石至暨陽,綿亙六七百里,統是陳艦列營,嚴加備禦。太子劭出鎮石頭,總統水師。丹陽尹徐湛之,往守石頭倉城。吏部尚書江湛,兼職領軍,軍事處置,悉歸調度。宋主親登石頭城,面有憂色,旁顧江湛在側,便與語道:“北伐計議,本乏贊同,今日士民怨苦,並使大夫貽憂,回想起來,統是朕的過失,愧悔亦無及了!”江湛不禁赧顏,俯首無詞。宋主復嘆道:“檀道濟若在,豈使胡馬至此!”誰叫你自壞長城? 嗣又轉登幕府山,觀望形勢,自思重賞之下,當有勇夫,因即榜示軍民,有能得魏主首,封萬戶侯,或梟獻魏王公首,立賞萬金。又募人齎野葛酒,置空村中,誘令魏人取飲,俾他毒死。統是兒女子計策。偏偏所謀不遂,智術兩窮。還幸魏主無意久持,遣使攜贈橐駝名馬,請和求婚。宋主亦遣行人田奇,答送珍羞異味。魏主見有黃柑,當即取食,且大進御酒。左右疑食中有毒,密戒魏主,魏主不應,但出雛孫示田奇道:“我遠來至此,並非貪汝土地,實欲繼好息民,永結姻援。汝國若肯以帝女配我孫,我亦願以我女配武陵王,從此匹馬不復南顧了!”田奇乃歸白宋主。宋廷大臣,多半主張和親,獨江湛謂戎狄無信,不如勿許。忽有一人搶入道:“今三王在阨,主上憂勞,難道還要主戰麼?”這數語的聲浪,幾乎響徹殿瓦,豺狼之聲。害得江湛大驚失色,慌忙審視,進言的不是別人,乃是太子劉劭。自知此人難惹,便即匆匆退朝。劭且顧令左右,當階擠湛,幾至倒地,宋主看不過去,出言呵禁,劭尚抗聲道:“北伐敗辱,數州淪破,獨有斬江、徐二人,方可謝天下!”宋主蹙額道:“北伐原出我意,休怪江、徐!”汝肯認過,怪不得後來遇弒?劭怒尚未平,悻悻而出。 可巧魏主也不復請和,但在瓜步山上,過了殘年。越日已爲元嘉二十八年元旦,魏主大集羣臣,班爵行賞,便下令拔營北歸。道出盱眙,魏主又遣使入城,饋送刀劍,求供美酒。守將臧質,卻給了好幾壇,交來使帶回。魏主酒興正濃,即命開封取酒,哪知一股臭氣,由壇衝出。仔細驗視,並不是酒,乃是混濁濁的小溲!臧質亦太惡作劇。 魏主大怒,便令將士攻城,四面築起長圍,一夕即就。且運東山土石,填砌濠塹,就君山築造浮橋,分兵防堵,截斷城中水陸通道。一面貽臧質書道: 爾以溲代酒,可謂智士,我今所遣攻城各兵,盡非我國人,城東北是丁零與胡,南是氐羌,設使丁零死,正可減常山趙郡賊;胡死可減幷州賊;羌死可減關中賊;爾若能盡加殺戮,於我甚利,我再觀爾智計也! 臧質得書,亦復報道: 省示具悉奸懷!爾自恃四足,屢犯邊境,王玄謨退於東,申坦散於西,爾知其所以然耶?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?蓋卯年未至,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!冥期使然,非復人事。我受命掃虜,期至白登,師行未遠,爾自送死,豈容復令爾生全,饗有桑乾哉!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;不幸則生遭鎖縛,載以一驢,直送都市耳!我本不圖全,若天地無靈,力屈於爾,齏之粉之,屠之裂之,猶未足以謝本朝。爾智識及衆力,豈能勝苻堅耶!今春雨已降,兵方四集,爾但安意攻城,切勿遽走!糧食乏者可見語,當出廩相遺。得所送劍刀,欲令我揮之爾身耶?各自努力,毋煩多言! 魏主接閱復書,當然大怒,特製鐵牀一具,上置許多鐵鑱,彷彿與尖刀山相似。且咬牙切齒,指牀示衆道:“破城以後,誓生擒臧質,叫他坐在鑱上,嘗試此味!”臧質得知消息,亦寫着都中賞格,有斬佛狸首封萬戶侯等語。魏主益怒,麾兵猛攻,並用鉤車鉤城樓。臧質將計就計,命守卒數百人,各執巨絙,將他來鉤繫住,反令車不得退。相持至夜間,質見魏兵少懈,縋桶懸卒,出截各鉤,悉數取來。次日辰刻,魏主改用衝車攻城,城土堅密,頹落不多。魏兵即肉薄登城,更番相代,前仆後繼,質與沈璞分段扼守,飭用長矛巨斧,或戳或斫,一些兒沒有放鬆。可憐魏兵只有下墜,不能上升,究竟性命是人人所惜,死了幾十百個,餘外亦只好退休。今日攻不下,明日又攻不下,好容易過了一月,仍然不下,魏兵倒死了萬餘人。春和日暖,屍氣薰蒸,免不得釀成疫癘,魏兵多半傳染,均害得骨軟神疲。探得宋都消息,將遣水軍自海入淮,來援盱眙,並飭彭城截敵歸路,魏主知不可留,乃毀去攻具,向北退走。 盱眙守將欲追躡魏兵,沈璞道:“我軍不過二三千名,能守不能戰,但教佯整舟楫,示欲北渡,能使虜衆速走,便無他慮了!”可行則行,可止則止,是謂良將。魏主聞盱眙具舟,果然急返,路過彭城,也無暇住足,匆匆馳去。彭城將佐,勸義恭出兵追擊,謂虜衆驅過生口萬餘,當乘勢奪回。義恭很是膽怯,不肯允議。 越日詔使到來,命義恭盡力追虜,是時魏兵早已去遠,就使有翅可飛,也是無及。義恭但遣司馬檀和之馳向蕭城,總算是奉詔行事,沿途一帶,並不見有魏兵,但見屍骸累累,統是斷脰截足,狀甚可慘。途次遇着程天祚,乃是由虜中逃歸,報稱南中被掠生口,悉數遭屠,丁壯都斬頭斬足,嬰兒貫諸槊上,盤舞爲戲,所過郡縣,赤地無餘,連春燕都歸巢林中,說將起來,真是可嘆!誰生厲階,一至於此?還有王玄謨前戍碻磝,也由義恭召還,碻磝仍被魏兵奪去。 看官聽着!這廢王劉義康,就在這戰鼓聲中了結生命。當時故將軍胡藩子誕世,擬奉義康爲主,糾集羽黨二百餘人,潛入豫章,殺死太守桓隆之,據郡作亂。適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卸職歸來,道出豫章,號召兵吏,擊斬誕世,傳首建康。太尉江夏王義恭,引和之爲司馬。且奏請遠徙義康,宋主乃擬徙義康至廣州。先遣使人傳語,義康答道:“人生總有一死,我也不望再生,但必欲爲亂,何分遠近?要死就死在此地,已不願再遷了!”宋主得來使返報,很是介意。及魏兵入境,內外戒嚴,太子劭及武陵王駿等,恐義康乘隙圖逞,屢把大義滅親四字,申勸宋主。宋主遂遣中書舍人嚴龍,持藥至安成郡賜義康死。如前誓何?義康不肯服藥,蹙然道:“佛教不許自殺,願隨宜處分。”零陵王曾有此語,不意於此復得之,劉裕有知,亦當悔弒零陵。嚴龍遂用被掩住義康,將他扼死。死法亦與零陵相同。 太尉江夏王義恭,徐州刺史武陵王駿俱因御虜無功,致遭譴責,義恭降爲驃騎將軍,駿降爲北中郎將。青、冀刺史蕭斌,將軍王玄謨,亦坐罪免官。自經此次宋、魏交爭,南兗、徐、兗、豫、青、冀六州,邑里爲墟,倍極蕭條。元嘉初政,從此濅衰了。小子有詩嘆道: 自古佳兵本不祥,況聞將帥又非良; 六州殘破民遭劫,畢竟車兒太不明!車兒系宋主義隆小字。 兵爲禍始,身且兇終。過了一兩年,南北俱有重大情事,出人意表。小子當依次演述,請看官續閱下回。 ------------- 觀張暢之出報魏使,措詞敏捷,可稱爲外交家。觀臧質之復答魏書,下筆詼諧,可稱爲滑稽派。但吾謂寧效張暢,毋效臧質。張暢所說,不亢不卑,能令魏使李孝伯自然心折,三寸舌勝過十萬師,張暢有焉。臧質以溲代酒,殊出不情,所致復書,語語挑動敵怒,曩令沈 璞無備,區區孤城,豈能長守!且使魏主無意北歸,誓拔此城,彭城又不敢發兵相救,則援絕勢孤,終有陷沒之一日,恐虜主所設之鐵牀,難免質之一坐耳。然則張暢之卻敵也,得之於鎮定;臧質之卻敵也,得之於僥倖,鎮定可恃,僥倖不可恃,臧質一試見效,至欲再試三試,宜後來之發難江州,一跌赤族也。
話說南朝宋廷緊急下詔,命柳元景等將領返回關中,詔書中大體意思是:由於王玄謨出征失敗撤軍,因此柳元景等人不應單獨前進,應即刻東歸。柳元景無法違抗聖旨,只得收兵退回,命令薛安都斷後,然後返回襄陽。
這次撤退,使得北魏軍隊得以集中力量南下,結果導致南朝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將領,慘遭戰死。
原來,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曾派參軍胡盛之從汝南出擊,梁坦從上蔡出發,攻打長社,又派司馬劉康祖進逼虎牢關。北魏永昌王拓跋仁偵察到懸瓠城空虛,一鼓作氣攻入,又攻陷了項城。恰好此時,宋廷下令各路軍隊迴歸本鎮,劉康祖與胡盛之便一同撤軍返程。行至威武鎮時,後方的北魏軍隊卻如潮水般蜂擁而至。胡盛之急忙對劉康祖說:“敵軍數量很多,遠遠望去不下數萬騎,我軍只有八千人,兵力懸殊,難以抗衡,看來只有依山靠險,走小路向南逃,纔不至於被俘。”劉康祖卻勃然大怒:“本來在河邊觀望,沒有主動作戰,現在敵人主動來送死,正是與他們正面交鋒的好機會,怎能戰前就心生怯懦?”他雖勇敢卻缺乏智謀,於是決定結車爲營,面向北方等待敵軍,同時下令軍中:“誰觀望不前,就處斬!誰驚慌退卻,就斬足!”士兵們也齊聲應令。話音未落,北魏軍隊已經殺到,四面圍攻,將宋軍團團包圍。宋軍拼死抵抗,從早晨打到傍晚,斬殺北魏士兵上萬人,血流至腳踝,劉康祖本人身中數創,仍鎮定自若,繼續指揮軍隊激戰。傍晚時分風起,北魏主帥拓跋仁命騎兵下馬,揹負乾草,放火焚燒劉康祖的車營。劉康祖邊燒邊補,親自指揮,卻有一支箭飛來,穿透了脖子,鮮血直流,當場暈倒,氣絕而亡。餘部再無法支撐作戰,由胡盛之率殘部數百人突圍逃回壽陽,八千將士傷亡過半。
北魏乘勝攻佔威武鎮,該鎮守將王羅漢手下僅有三百士兵,哪裏抵擋得住數萬敵騎,很快便被圍困,無法突圍,最終被俘。北魏將領三郎將把王羅漢鎖住,並派人看守。到了半夜,王羅漢瞅準三郎將睡覺的時機,扭斷鐵鏈,悄悄走到其身旁,偷取佩刀,砍下其頭,抱鎖出營,飛快逃到盱眙,僥倖保全性命。
拓跋仁繼續逼進壽陽,南平王劉鑠登上城頭固守。北魏皇帝拓跋燾則將豫州軍務全部交給永昌王拓跋仁,自己親率精銳騎兵前往徐州,直逼蕭城。先前寫到宋軍出發時氣勢浩大,如今卻反客爲主,可見戰爭勝負無常,令人驚心。蕭城距離彭城僅十餘里。彭城兵力雖多,但糧草不足,江夏王義恭擔心無法守住,便打算放棄城池南撤。沈慶之則認爲歷城糧草充足,建議攜帶兩位王爺和王妃、公主,直奔歷城,留下護軍蕭思話鎮守。長史何勳反對此議,主張東奔鬱洲,乘海路繞道回建康。只有沛郡太守張暢得知兩方意見爭執不下,立即去見義恭,說:“歷城和鬱洲,既無法前往,也很難抵達。想想城中早已斷糧,百姓早已想要離開,只是因爲城門關閉,無路可走,一旦主帥一走,軍隊必定潰散,敵軍從後追擊,還能逃到歷城或鬱洲嗎?如今我們雖糧草不足,但還能支撐一個月,哪能爲了眼前之安而捨棄生命,自投死路?如果兩方意見一定要實行,我願先以頭顱濺血,玷污你們的馬蹄!”話音剛落,武陵王駿也進言:“叔父統帥大軍,選擇去或留,本非我等百姓可干預的。我是駿的幼名。如今若讓主將出逃,我還有什麼臉面回朝廷見人?城存我存,城亡我亡,我願聽從張太守之言,誓死不走!”正是由於這番話,南朝的皇帝才終於決定不撤離。
北魏主拓跋燾到達彭城後,就在戲馬臺搭建氈房,眺望城中情況。看到守軍列陣整齊,器械精良,他也不敢貿然進攻,於是派尚書李孝伯前往南門,送了貂皮大衣一件,還送了馱馬和騾子幾頭,並對義恭說:“魏主致意安北將軍,可暫且出城相見,我不過是來看望,無意攻城,何必如此嚴陣以待?”武陵王駿曾擔任安北將軍,擔心魏主心懷不軌,於是派張暢出城報信,與李孝伯會談,說:“安北將軍武陵王非常想見魏主,但臣子沒有外交權,彼此本是平等,守城是城主要負責之事,何須多疑?”
李孝伯回稟魏主後,魏主請求酒和橘子、蔗糖,並借取博戲用具,武陵王駿一一滿足。魏主又贈送毛氈、胡鹽和九種鹽,請求借樂器。義恭再次派張暢出城回答。張暢一出城,城內守將見魏國尚書李孝伯騎馬而來,便立即拉起吊橋,關閉城門。李孝伯與張暢會面後,張暢立即傳話:“我太尉江夏王受命統軍,未帶樂器,故無法配合。”李孝伯說:“這沒什麼,但你一出城,爲何立刻關閉城門?”張暢未等說完,便直接答道:“二王擔心魏主初到,營地尚未建立,將士勞頓疲憊,城中尚有十萬精兵,怕他們因憤怒出城,輕率進攻,因此關閉城門阻止,不讓他們輕易交戰。待魏主安頓好軍隊,雙方交換戰書,再指定戰場,一決勝負。”這種從容鎮定的氣度,頗有像晉代欒鍼的風采。
李孝伯正要回答,忽然又有魏主派使者趕來,對張暢說:“致意太尉安北,爲何不派人來我軍營?哪怕話語不充分,也請見見我,看看我的身材、年齡,瞭解我的爲人,究竟如何?如果諸位輔佐都不願派去,也可以派僕從前往。”張暢回答:“魏主的容貌和能力,早已耳聞,李尚書親來傳達,我們已可坦誠對話,因此不再另派使節了。”
李孝伯又說:“王玄謨是個庸才,南方爲什麼會重用他,以致戰敗?我軍入境七百里,主人居然不發一箭相迎,我想這彭城也未必能長久守住吧!”張暢反駁說:“王玄謨只是南地邊將,不過是前驅之用,並非核心將領。只是因爲大軍尚未到達,河道結冰,他趁夜撤軍,是出於商討退路的計策,部下未察,稍有誤行,哪裏有什麼重大損失?若魏軍入境七百里,無人抵抗,那是因爲我太尉的謀略,鎮軍的祕計,用兵有章法,不便公開。”他巧妙地爲自己開脫,自圓其說。
李孝伯又換了一種說法:“魏主原無攻城之意,本打算率大軍直取瓜步,若一路順利,彭城何必再攻?萬一失敗,這城對我們也無用,我將南下飲江邊之水,解解口渴!”張暢微笑着說:“去留都聽你安排,不過北馬飲江,恐怕觸犯天忌;若真如此,那便是沒有天道了!”這句話讓李孝伯大喫一驚。原來古代有童謠說:“北魏騎兵飲江水,佛狸將在卯年死。”這一年正是辛卯年,因此李孝伯聽了之後心驚。他便對張暢說:“您深明大義,我們相距不遠,真想握手言和!”張暢回道:“李尚書請保重,將來中原平定,您是漢人,屆時可歸我朝,相聚的日子定會到來!”說完一拱手,便分道而別。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人才。
第二天,魏主下令攻城,城上箭石如雨,擊傷大量魏軍士兵。魏主於是改道南下,派中書郎魯秀出廣陵,高涼王拓跋那出山陽,永昌王拓跋仁出橫江,所經城池無不是殘破不堪。江淮地區震驚,建康城內緊急戒嚴。宋文帝隨即任命臧質爲輔國將軍,率一萬兵馬救援彭城。臧質行至盱眙,得知魏軍已越過淮河,急忙派偏將臧澄之、毛熙祚分別駐守東山和前浦,自己則在城南紮營。然而,臧、毛兩處營地接連被北魏軍隊攻破,燕王拓跋譚率軍直逼臧質營地。臧質軍陣驚亂,僅剩七百人,隨他逃往盱眙城,所有糧草器械全部丟棄。
盱眙太守沈璞上任不久,就修繕城池,疏通護城河,儲備糧草,兵器刀矛箭矢一應俱全。當時部下都覺得他多此一舉,等到魏軍逼近,又勸他逃往建康。沈璞堅定地說:“我此前籌備守備,正是爲了今天。如果敵人遠道而來,認爲城小,不願進攻,那也用不着多勞。倘若他們強攻城牆,這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刻,也是你們立功封侯的機會!你們可曾聽說過昆陽、合肥的事例嗎?新莽、前秦都集結數十萬大軍,卻在昆陽、合肥被擊潰,一敗塗地,哪裏見過幾十萬大軍在小城下長期堅守而未被打敗?”部下聽後,才真正有了堅守的信心。
沈璞招募了兩千精銳士兵,閉城待敵。等到臧質來攻打時,部下又勸他不要接見,沈璞嘆息道:“同舟共濟,胡越一心,何況兵衆輕易就能擊敗敵軍,怎能拒之門外?我願開放城門迎接臧將軍!”於是打開城門接納臧質。臧質進入城內,看到城防完備、物資充足,非常喜悅,當即與沈璞立誓共守城市,民衆紛紛歡呼萬歲。
北魏軍隊沒有帶足糧草,靠沿途劫掠維持軍需。進入淮南後,百姓紛紛逃亡,沿途無法掠奪,士兵疲憊不堪,又遭遇饑荒,聽說盱眙有大量存糧,便迫不及待希望攻城,飽飽地帶走。偏偏攻城未能得逞,使得魏主無計可施,只好留下數千人駐守盱眙,自己率大軍南下。
行至瓜步,魏軍毀壞民房,取材製作浮橋,因材料不足,便用竹葦補充。他們聲稱要渡江深入,建康上下頓時驚慌。宋文帝立即命令領軍將軍劉遵考等人,分兵扼守江上渡口,從採石到暨陽,綿延六七百里,佈設戰艦,嚴密防守。太子劉劭鎮守石頭城,統領水師。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。吏部尚書江湛兼任領軍,負責軍事調度。宋文帝親自登上石頭城,面帶憂色,看到江湛在側,便對他說:“北伐本無衆人支持,如今百姓怨聲載道,使你我也憂心,回想起來,這全是朕的過錯,後悔也來不及了!”江湛頓時羞愧,低頭無言。宋文帝又嘆道:“如果檀道濟在世,豈會容許胡馬至此?”可惜你親手毀掉了長城。
後來,他再次登上幕府山觀察地形,心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,於是張貼告示,宣稱誰能斬獲魏主首級,封萬戶侯;誰斬殺魏王或公爵首級,賞萬金。還招募人攜帶野葛酒,藏在空村中,引誘敵軍飲用,讓其中毒。這些全是孩童般的計策。但計劃全都失敗,智謀也徹底破產。好在魏主無意久留,派使者攜帶駱駝、名馬前來求和,請求聯姻。宋文帝也派行人田奇回禮,贈送珍饈美味。魏主看到黃柑,當場品嚐,還大飲美酒。手下將領懷疑酒中有毒,密勸魏主不要喝,魏主不聽,反而拿出自己的小孫子給田奇看,說:“這是我家小孫,也來見見。”魏主於是與田奇建立了友好關係。
但不久,魏主得知宋軍要從水路支援盱眙,又命彭城切斷敵軍退路,便知道不可久留,於是撤去攻城器具,向北撤退。
盱眙守將想追擊北魏,沈璞說:“我們兵力只有二三千人,只能守城,不能打仗,只需假裝整修船隻,示意向北渡江,就能讓敵軍迅速撤退,便沒有後顧之憂。”這就是真正優秀的將領——能進能退,隨機應變。魏主得知盱眙有船,果然緊急撤退,路過彭城,也沒時間停留,倉皇北去。彭城將領勸義恭立即追擊,稱敵軍擄走生口一萬多人,應趁勢奪回。義恭卻膽怯,不肯答應。
第二天,詔書抵達,命義恭全力追擊,但此時魏軍早已遠去,即使有翅膀也無法追上。義恭只派司馬檀和之前往蕭城,也算完成任務,途中所見的,全是屍體累累,全是被砍頭、斷足的慘狀。途中遇到程天祚,是逃回的平民,他說南地被掠的百姓,全被屠殺,壯年被斬頭砍足,嬰兒被釘在長矛上,繞着玩樂,所過之處,田地荒蕪,連春燕也都飛回巢中,令人痛心!誰生出這等災難?還有王玄謨之前駐守碻磝,也被義恭召回,碻磝最終仍被北魏奪走。
各位請注意,這一戰中,被廢的劉義康,也在戰亂中結束生命。當時將軍胡藩的兒子胡誕世,謀劃擁立劉義康爲主,集結黨羽二百餘人,潛入豫章,刺殺太守桓隆之,佔據郡縣作亂。恰逢交州刺史檀和之卸職歸來,途經豫章,召集兵士,誅殺胡誕世,將首級送至建康。太尉江夏王義恭因此任命檀和之爲司馬,並上奏請求將劉義康遠遷。文帝於是擬將劉義康遷至廣州。先派使者傳達,劉義康回答說:“人生終有一死,我不指望活着,但若要造反,遠近都一樣。要死,就死在這兒,我已不願再搬遷了!”文帝聽說後很爲所動。後來魏軍入侵,內外戒嚴,太子劉劭和武陵王駿等人擔心劉義康趁機作亂,一再勸說文帝“大義滅親”。文帝於是派中書舍人嚴龍,帶藥到安成郡賜死劉義康。劉義康拒絕服藥,說:“佛教不許自殺,願依佛教處理。”零陵王曾說過這句話,想不到在此重演。嚴龍便用被子捂住他,將其扼殺。死法也和零陵王一樣。
太尉江夏王義恭、徐州刺史武陵王駿因抗擊外敵無功,被貶責,義恭降爲驃騎將軍,駿降爲北中郎將。青、冀刺史蕭斌和將軍王玄謨也因罪被罷免官職。自這起宋魏交鋒後,南兗、徐、兗、豫、青、冀六州,變成廢墟,極度荒涼,國家元氣大傷。元嘉初年的盛世,從此衰落。
小詩嘆曰:
自古戰爭本不祥,何況將領又非良;
六州殘破民遭劫,終究是車兒太不明!
(“車兒”是宋文帝劉義隆的小名)
兵爲禍端,自身亦難逃敗亡。過了一兩年,南北都出現重大變故,出人意料。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裏一一講述,請繼續關注下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