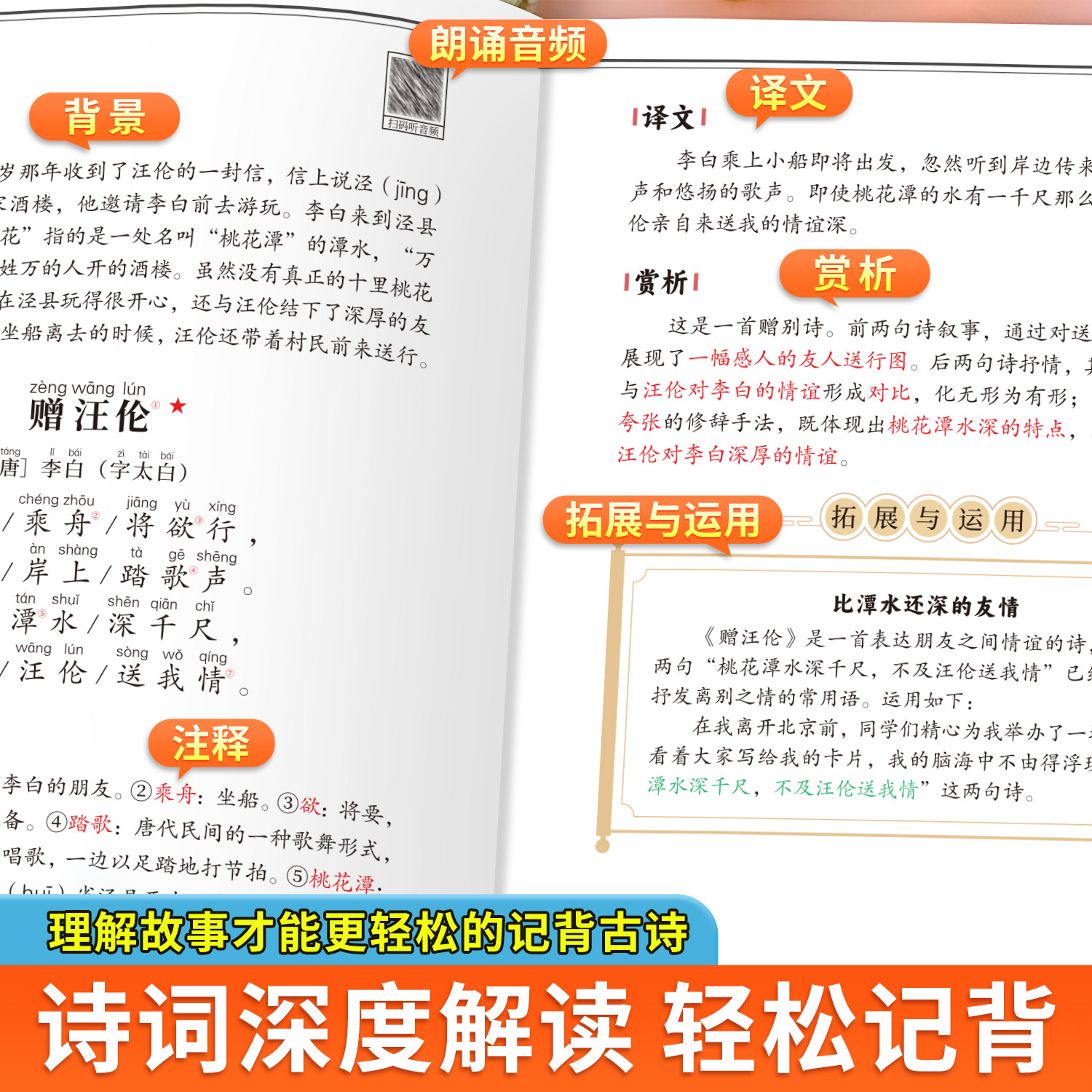《紅樓夢》-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譯文:
(故事版·現代漢語講述)
夏日的賈府,陽光正盛,寶玉剛從屋裏出來,手裏攥着一隻麒麟,眼睛亮得像星星。他高興地笑了:“你倒是揀了個好東西,真是撿到寶了!”史湘雲調皮地回他:“虧你揀上啦!要是個印都丟了,那可麻煩了,這麒麟可是頂要緊的啊!”寶玉一聽,直拍大腿:“要是丟了這個,我活不了,得死!”
這時,襲人端來茶,笑着對史湘雲說:“大姑娘,你前兩天可真高興,都說你嫁了個好人家,還恭喜你呢。”史湘雲一聽,臉紅得像番茄,低頭喝茶,一句話也不說。襲人看着她,笑道:“這會兒又害羞了?你還記得十年前,我們住在西邊暖閣裏,晚上你哄着我,給我梳頭、洗臉,還跟我講悄悄話的時候嗎?那時候你可沒這麼扭捏,怎麼現在一提就臉紅呢?”
史湘雲一聽,忍不住笑出聲:“你可別說啦,那會兒我們多親熱,誰家姐妹比得上呢?後來我母親走了,我們家搬去住了一陣,你反倒被分派去照顧二哥哥,我來了,你也不像從前那樣待我了。”
襲人反手一樂:“你又說這些!當初姐姐們哄着我,天天讓我替你做這做那,現在你長大了,就擺出小姐派頭來,我怎麼敢親近你呢?”
史湘雲嘆了口氣,說:“阿彌陀佛,冤啊冤哉!要是真像你說的那樣,我立刻就死了!你瞧,這大太陽天,我一到這兒,就特意趕來看你,不信問問問我屋裏那個叫縷兒的丫鬟,我回家時哪一回不念你幾聲?”
話沒說完,寶玉和襲人都急忙勸道:“你又說大話了,別當真啊,性子這麼急是不行的。”
史湘雲不服氣:“你不說你的話噎人,還說我性急?”
兩人一邊說着,一邊打開手帕,把一枚戒指輕輕遞給了襲人。襲人感動得直說:“謝謝呀,這麼珍貴的東西,我真沒想到你會親自送來……這戒指不值幾個錢,可它代表的心意,比金子還重。”
“這戒指是誰給你的?”史湘雲問。
“是寶姑娘給我的。”襲人答。
“我以爲是林妹妹給你的,原來是寶釵姐姐。”史湘雲眼睛一紅,聲音哽咽,“我天天在家裏都想,咱們這些姐妹裏,沒有一個比寶姐姐更好的。可惜啊,我們不是一母同胞!要是我也有這麼個親姐姐,就算沒了父母,我也能安心活一輩子。”
說着說着,她眼淚就流下來了。
寶玉忙擺手道:“罷了罷了,別提這事了!”
史湘雲卻說:“提這個又有什麼不對?我知道你心裏藏着什麼,怕林妹妹聽見我誇寶姐姐,又要生你的氣。可這不就是因爲你心裏的事,才這麼怕嗎?”
這時,襲人笑了一聲,說:“雲姑娘,你長大了,越來越直爽了!”
寶玉嘆了口氣,說:“我早就說你們這幫人說話難懂,果然沒錯。”
史湘雲立刻反駁:“好哥哥,你別說得我心慌!你在我們面前還能說笑,可一見林妹妹,就變了臉色,不知怎麼地就冷下來。”
襲人又說:“先別說這些無聊的,我還有個事想求你。”
“什麼事?”史湘雲問。
“有一雙鞋,墊子被摳壞了,我這兩天身子不舒服,沒法做,你有沒有空幫我縫一縫?”
史湘雲笑道:“你家可是有好幾個巧手丫鬟,針線活兒都快成家業了,怎麼還讓我動手?你的活,誰不做誰不地道!”
襲人眨了眨眼:“你可太糊塗了!我們屋裏針線,可不是誰都能做的,是得專門留着給寶玉的。”
史湘雲一聽,立刻明白了,笑着說:“既然這樣,我幫你做吧。但有個條件——我的針線只爲你做,別人我可不去沾邊。”
襲人一笑:“又來了,我是什麼人,還請你去做鞋?告訴你吧,不是我的!你別管是誰的,只要說聲‘領情’就行。”
史湘雲沉吟道:“按理說,你該早請我做過不少東西,今天反倒不做了,你肯定知道原因。”
襲人愣了下:“我倒真不知道。”
史湘雲冷冷一笑:“前天我聽說,你把我的扇套子拿去跟別人比,後來還賭氣剪了兩段!我早就知道了,你卻瞞着我。現在又讓我做,我豈不是成了你們的‘奴才’?”
寶玉趕緊插話:“那件事情,我根本不知道是你做的!”
襲人也笑了:“是啊,是我騙他,說最近有個會做活的女孩,做的花特別漂亮,我讓他拿扇套子試試。他信了,到處拿去給人看。結果惹惱了林姑娘,剪了兩段。後來他非得馬上補,我才說是我做的,他當時後悔得不行。”
史湘雲說:“真是越想越奇怪!林姑娘又何必生氣?她會剪,爲什麼不讓她自己做?”
襲人說:“她壓根兒就不做啊!老太太還生怕她太過勞累,醫生也說要靜養,誰會去煩她?去年一年才做了個香袋,今年半年都沒碰針線呢!”
正說着,有人來報:“興隆街的爺來了,老爺叫二爺出去見面。”
寶玉一聽,心一下子沉了下去——那是賈雨村啊,他最討厭見這種人。他一邊穿鞋,一邊抱怨:“有老爺坐那兒就好,怎麼老要我見他?”
史湘雲搖着扇子,笑着說:“你不是能說會道的嗎?老爺才叫你去呢!”
寶玉說:“哪裏是老爺,是他自己非要請我去見的。”
湘雲笑道:“主家高雅,客人勤來,自然你有本事吸引他們,他纔想見你。”
寶玉嘆氣:“罷了罷了,我哪兒夠得上‘雅’啊,不過是個俗人,根本不想跟這些人往來。”
湘雲笑着說:“你還是老樣子啊。現在都大了,不去讀書考科舉,也不懂仕途上的事,連和人談講一下‘官場經濟學’都沒機會,將來怎麼應付人情世故?你不是總在我們這兒胡鬧嗎?”
寶玉立刻反駁:“姑娘請別的姐妹去坐坐,別讓我毀了你那些‘經濟學’!”
襲人趕緊勸:“雲姑娘,可別說這種話!上回寶姑娘也說了一句話,結果她一咳,就抬腳走了,寶姑娘說完話,見她走,臉都紅了,說說不尷尬,不說又覺得不對。幸虧是寶姑娘,要是林姑娘,怕是當場哭得稀里嘩啦。可後來她還是像從前一樣,真是有涵養,心地寬厚。我真沒想到,你這一下反倒跟她冷淡了!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她,你得賠多少不是啊!”
寶玉說:“林姑娘什麼時候說過這種話?要是她也這樣說,我早跟她鬧翻了!”
襲人和湘雲都點頭:“這話說得確實不講理。”
其實啊,林黛玉早就知道史湘雲和寶玉在一塊兒,也猜到寶玉最近迷上了那些外傳的野史——說才子佳人,都是因爲一個小小物件撮合的,比如鴛鴦、鳳凰,或者玉環金佩、鮫帕鸞絛,都是從小物件起頭,最後走到一起。
如今見寶玉手上有了麒麟,她心裏直打鼓:會不會又藉着這個,和史湘雲偷偷發展出點什麼風流事?
於是她悄悄溜過來,聽他們說話。沒想到,正聽見史湘雲說“經濟”這些俗事,寶玉還說:“林妹妹從沒說過這些混話,要是她說,我也要跟她絕交!”
林黛玉聽了,心裏像被雷擊中——高興,驚訝,悲傷,又嘆氣。
高興的是,自己確實看對了人,一直以爲他是個知己,果然不假;驚訝的是,他居然在人前誇我、說私話,那份親熱,連嫌疑都不怕;悲哀的是,既然你我都是彼此的知己,那還說什麼“金玉良緣”?既然都彼此瞭解,那爲什麼要另起爐竈?爲什麼還要去提寶釵?
更讓人心碎的是,父母早逝,平時說的那些心話,沒人替我說過。如今我常常神思恍惚,病也越來越重,醫生說我是氣弱血虧,怕將來身體垮掉。你我雖是知己,但怕我活不了多久——你就算懂我,又怎麼能爲我撐起一片天呢?
想到這裏,她眼淚嘩嘩地流下來。
她想着要進去見寶玉,卻覺得無味,便一邊擦淚,一邊轉身回去了。
寶玉一出來,就看見黛玉慢慢走着,眼角含淚,連忙追上前,笑着說:“妹妹去哪兒了?怎麼又哭了?是哪個惹你生氣?”
黛玉回頭,勉強笑道:“好好的,我沒哭啊。”
寶玉一看,她眼睛裏分明還掛着淚,笑着說:“你看,眼淚都沒幹,還說謊呢!”
說着,他不由自主伸手去擦黛玉的淚。
黛玉嚇得一退,大聲道:“你又想死啦?幹嘛動手動腳的!”
寶玉笑道:“說話沒分寸,不自覺就動了,顧不得死活。”
黛玉又說:“你要是死了,倒也不可惜,可丟了金,又沒了麒麟,那可怎麼辦?”
一句話徹底把寶玉激得急了,他衝上去問:“你到底是在咒我,還是在氣我?”
黛玉一聽,立刻想起前日的事,心裏一慌,連忙笑着補救:“別急,我剛纔說錯了,哪有這種事,我一激動,心都跳得亂了,臉都出汗了。”
說着,她又忍不住走過來,輕輕替寶玉擦掉臉上的汗。
寶玉盯着她看了半天,終於說:“你放心。”
黛玉聽了,怔住,半天才說:“我有什麼不放心的?我不懂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?”
寶玉嘆了口氣,認真道:“你真的不明白?難道我這些年來對你的用心都白費了?如果你根本沒讀懂我,那我天天給你發脾氣,你天天爲我生氣,也難怪了。”
黛玉點頭:“我真不明白,你說的‘放心不放心’,到底是什麼意思?”
寶玉嘆道:“好妹妹,你別哄我!如果你真不明白,那我這些年來的心血就都白費了,你對我的好,也全都浪費了。你總是不放心,才弄出一身病來。要是我多安慰你幾句,你又怎麼會一天比一天更虛弱?”
黛玉聽了這話,像被雷劈中,心裏翻江倒海,比自己從心裏掏出來的話還真摯,她想說一千句,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,只是呆呆地望着他。
寶玉的心裏也像炸開一樣,他想說的話太多,卻一個字也說不出,只能怔怔地望着她。
兩人僵持着,黛玉只輕輕咳了一聲,眼淚猛地滾落,轉身就走。
寶玉急忙追上去,拉住她:“好妹妹,先別走,我有句話要對你說完。”
黛玉一邊擦淚,一邊推他:“有什麼好說的?我早知道了啊!”說着,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寶玉一個人站在原地,愣了半天。
他出門着急,忘了帶扇子。襲人怕他中暑,趕緊追上來,遞扇子給他,抬頭一看,見黛玉和他站在一起,黛玉剛走,他仍呆在那裏。
襲人見狀,笑着說:“你也不帶扇子,虧我看見,特地趕過來送你。”
寶玉出神,沒聽清是哪位,一把拉住襲人:“好妹妹,我這輩子最不敢說的心事,今天我豁出去了,說給全天下聽——我爲你弄了一身病,都不敢告訴別人,只能藏着。只盼着你病好了,我的病纔好。睡裏夢裏,我都沒法忘了你!”
襲人嚇得魂飛天旋,大聲叫道:“天啊!神仙保佑,我可被坑死了!”她趕緊推開寶玉:“這簡直是胡說八道!你中邪了?快回去!”
寶玉這才醒悟——原來是襲人送扇子,臉一下子紅得像火,一把奪過扇子,趕緊跑了。
此時,襲人看着他走遠,心裏發毛:剛纔那一番話,肯定是林黛玉引起的!如果真如此,將來恐怕會出大事,太可怕了。
她越想越怕,眼淚不由自主往下掉,心裏盤算着怎樣纔不會出亂子。正想着,忽然看見寶釵從那邊走來,笑着問:“太陽這麼大,怎麼愣着出神?”
襲人忙笑道:“我正看兩個小雀打架,太有趣了,我躲着看呢。”
寶釵問:“寶兄弟,你現在穿了衣服,怎麼這麼着急地跑出去了?我剛看見你走,想叫住你,可你說話越來越沒頭沒腦的,我就沒叫了。”
襲人說:“是老爺叫他出去的。”
寶釵一聽,嚇了一跳:“這麼燙的天,叫他去幹什麼?莫不是又想氣事,叫出去訓一頓?”
襲人笑說:“不是,是有人要見他。”
寶釵搖搖頭:“這種客人也沒意思,大太陽天,不回家涼快,跑什麼?”
襲人說:“你倒是說說看嘛。”
寶釵便問:“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?”
襲人笑說:“才聊了一會兒,你瞧,我前些天讓做的一雙鞋,明兒讓她說做。”
寶釵聽了,回頭看了看,確認沒人來,便笑道:“你這麼聰明的人,怎麼一時半會兒就體會不到人情?我最近看了雲丫頭,聽她說話,特別內含委屈。她家嫌花銷大,乾脆不用那些做活的丫鬟,大部分都是她孃兒幾個動手。她幾次來,見沒人,就說起家裏窮得不行,連我問一句家常,她眼圈就紅了,話也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來。我一看,就知道她從小就沒爹孃,太苦了。我看着都心疼。”
襲人聽後,一拍大腿:“啊!原來是這樣!我前些天叫她打十根蝴蝶結,過了好幾天纔派人送來,還說‘打得粗些,能用就行,要勻淨的,等我來了再好好打’。現在聽寶姑娘這麼說,我才明白,她其實很辛苦,不知她在家裏是不是三更半夜做活!早知道這樣,我也不該給她添麻煩。”
寶釵說:“上回她就告訴我,她在家做活做到三更天,要是替別人做點活,家裏那些奶奶太太還嫌不夠,非說不夠用。”
襲人嘆氣:“偏偏我們那個小少爺,性子倔,只做自己的事,家裏那些活兒根本不讓丫鬟碰。我又搞不定,也幫不上忙。”
寶釵笑着說:“你管他幹什麼?叫人做就是了,別說是我做的,就說你讓做的,他自然信。”
襲人說:“那可不是,他一眼就能看出破綻,我只能慢慢累着做。”
寶釵笑:“你別急,我來替你安排。”
話還沒說完,忽然一個老婆婆急匆匆跑來大聲說:“糟了!金釧兒姑娘,投井死了!”
襲人嚇了一跳,問:“哪個金釧兒?”
老婆婆說:“哪兒有兩個金釧兒?就是太太屋裏的那個!前天沒來上班,回家哭哭啼啼,沒人理她,後來找不見了。剛纔打水的人在東南角的井裏打水,看見一個屍體,趕緊打撈上來,是她!她家還鬧着要救人,哪能救得回來!”
寶釵說:“這也太奇了。”
襲人聽了,點頭嘆氣,想起和金釧兒的舊情,也不由自主流下眼淚。
寶釵趕緊勸:“姨娘,你也不必太難過,送幾兩銀子就過去了,主僕之情也就盡到了。”
王夫人說:“我剛賞了她娘五十兩銀子,本來要給她做兩套新衣服,結果鳳姐說沒有新做的,只有林妹妹過生日的兩套。我擔心林妹妹這麼敏感,說好過生日,現在又要給別人穿,不吉利。所以現在我讓人趕製兩套,要是別的丫鬟,賞點銀子就夠了,可金釧兒雖然只是丫頭,從小在我跟前,跟我的女兒也差不多。”
說着,她眼淚又掉了。
寶釵立刻說:“姨娘,何必再叫裁縫趕製?我前兩天已經做好兩套,拿來送她不就省事了?她活的時候穿過我的舊衣服,身量也差不多。”
王夫人猶豫:“可這樣不吉利嗎?”
寶釵笑着說:“姨娘放心,我從來不在乎這些講究!”
說罷,她轉身就走,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着她。
不一會兒,寶釵帶着衣服回來了,只見寶玉正坐在王夫人身邊,淚流滿面。
王夫人本來要數落他,可見寶釵進來,便立刻收了嘴。
寶釵一眼就看懂了氣氛,立刻把衣服交上去。
王夫人叫來她母親,把衣服拿去。
——下回再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