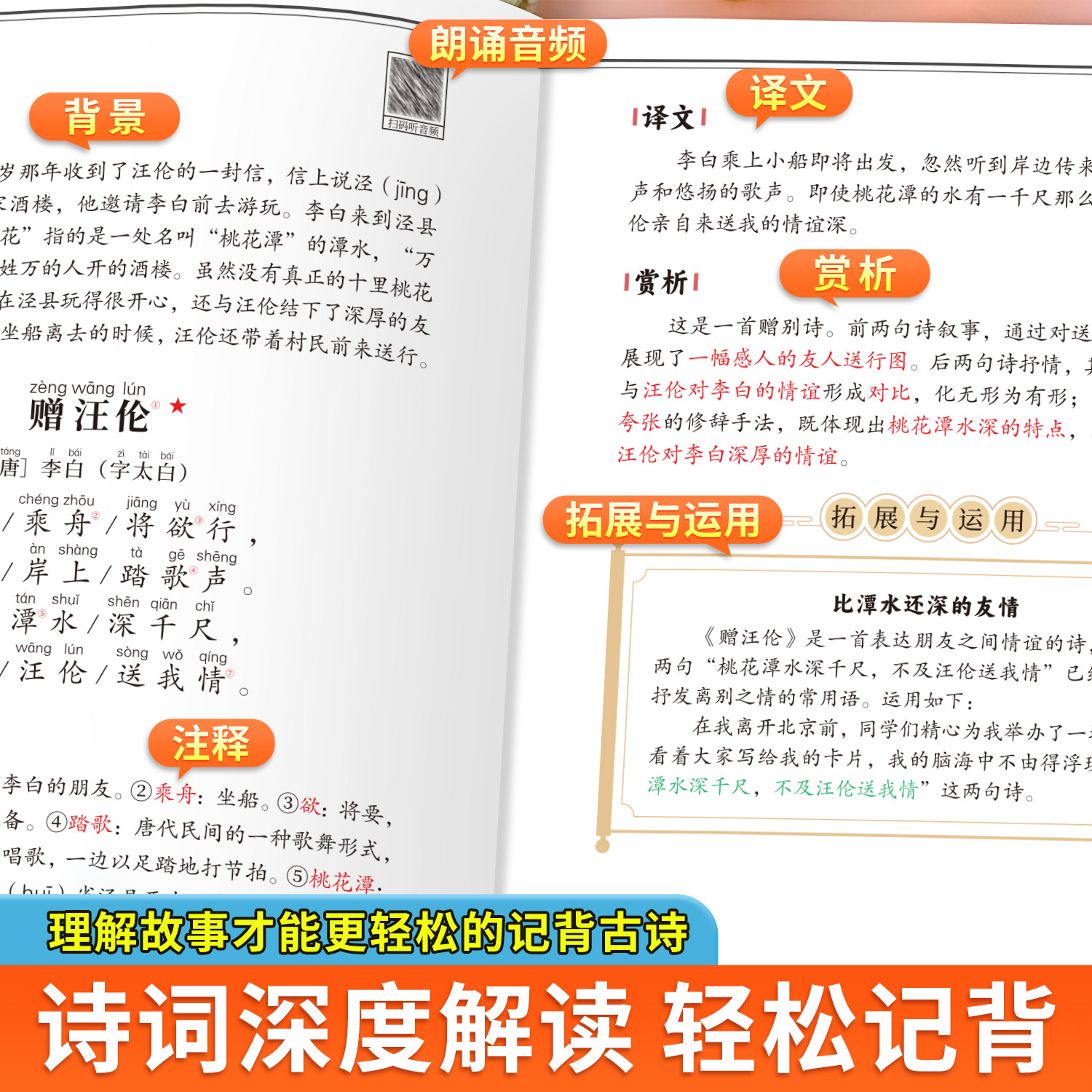卻說阿忽臺正欲抵敵,猛見一赳赳武夫,才知不是對手。這人爲誰?就是諸王禿剌。禿剌指揮衛士,來擒阿忽臺。阿忽臺只怕禿剌,不怕衛卒,衛卒上前,被他推翻數人,即欲乘間脫逃。禿剌便親自動手,把他截住。阿忽臺至此,雖明知不敵,也只好拚命與鬥。俗語說得好,棋高一着,縛手縛腳,況武力相角,更非他比,不到數合,已被禿剌撳住,飭衛士用鐵索捆好。那時安西王阿難答,及諸王明裏帖木兒,向沒有甚麼本領,早被衛士擒住。縛扎停當,押送上都,一面搜殺餘黨,一面禁錮皇后。 事粗就緒,諸王闊闊一作庫庫、牙忽都一作呼圖。入內,語愛育黎拔力八達道:“罪人已得,宮禁肅清,王宜早正大位,安定人心!”現成馬屁。愛育黎拔力八達道:“罪人潛結宮闈,亂我家法,所以引兵入討,把他伏誅,我的本心,並不要作威作福,窺伺神器呢。懷寧王是我胞兄,應正大位,已遣使奉璽北迎。我等只宜靜等宮廷,專待吾兄便了。” 當下哈喇哈孫議定八達監國,自統衛兵,日夕居禁中備變,並令李孟參知政事。李孟損益庶務,裁抑僥倖,羣臣多有違言。於是李孟嘆息道:“執政大臣,當自天子親用,今鑾輿在道,孟尚未見顏色,原不敢遽冒大任。”遂入內固辭,不獲奉命,竟掛冠逃去。 是時海山已自青海啓程,北抵和林,諸王勳戚,合辭勸進。海山道:“吾母及弟在燕都,俟宗親盡行會議,方可決定。” 乃暫行駐節,專候燕都消息。 先是海山母弘吉剌氏,嘗以兩兒生命,付陰陽家推算。陰陽家謂“重光大荒落有災,”“旃蒙作噩長久。”小子嘗考據爾雅,大歲在辛曰:“重光,”在巳曰:“大荒落,”是重光大荒落的解釋,就是辛巳年。又在乙曰:“旃蒙,”在酉曰:“作噩。”是旃蒙作噩的解釋,就是乙酉年。海山生年建辛巳,愛育黎拔力八達生年建乙酉。弘吉剌妃常記在心,因遣近臣朵耳往和林,傳諭海山道:“汝兄弟二人,皆我所生,本無親疏,但陰陽家言,運祚修短,不可不思!” 海山聞言,嘿然不答。既而召康裏脫脫進內,語他道:“我鎮守北方十年,序又居長,以功以年,我當繼立。我母拘守星命,茫昧難信,假使我即位後,上合天心,下順民望,雖有一日短處,亦足垂名萬世。奈何信陰陽家言,辜負祖宗重託!據我想來,定然是任事大臣,擅權專殺,恐我嗣位,按名定罪。所以設此奸謀,藉端抗阻。你爲我往察事機,急速報我!”星命家言原難盡信,但也未免急於爲帝。 康裏脫脫奉命至燕,稟報弘吉剌妃。弘吉剌妃愕然道:“修短雖有定數,我無非爲他遠慮,所以傳諭及此。他既這般說法,教他趕即前來罷。” 當下遣回脫脫,復差阿沙不花往迎。適海山率軍東來,途次遇着兩人。阿沙不花具述安西謀變始末,及太弟監國,與諸王羣臣推戴的意思。脫脫復證以妃言。海山大喜,即與二人同入上都,命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,遣他還報母妃又母弟。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奉母妃至上都,諸王大臣亦隨至,當即定議,奉海山爲嗣皇帝。 海山遂於上都即位,追尊先考答剌麻八剌爲順宗皇帝,母弘吉剌氏爲皇太后。一面宣敕至燕京,廢成宗後伯嶽吾氏,出居東安州,又將安西王阿難答,及諸王明裏帖木兒,與左丞相阿忽臺等,一併處死。嗣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伯嶽吾後同居禁中,嫂叔無猜,定有姦淫情弊,所以不立從子,反欲妄立皇叔,業已穢亂深宮,律以祖宗dafa,罪在不赦,應迫她自盡。詔書一下,伯嶽吾後無術可施,只好仰藥自殺了。垂簾亦無甚樂趣,爲此妄想,弄得身名兩敗,真是何苦! 海山後號武宗,因此小子於海山即位後,便稱他爲武宗。 當時改元至大,頒詔大赦。其文道: 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,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,列聖相承,不衍無疆之祚。朕自先朝肅將天威,撫軍朔方,殆將十年,親御甲冑,力戰卻敵者屢矣,方諸藩內附,邊事以寧。遽聞宮車晏駕,乃有宗室諸王,貴戚元勳,相與定策於和林,鹹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,裕宗正派之傳,以功以賢,宜膺大寶。朕謙讓未遑,至於再三,早已蓄謀爲帝,偏說謙讓再三,中國文字之欺詐,多半如此,可嘆!還至上都,宗親大臣,復請於朕。間者奸臣乘隙,謀爲不軌,賴祖宗之靈,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,稟命太后,恭行天罰。內難既平,神器不可久虛,宗祚不可乏嗣,合詞勸進,誠意益堅,朕勉徇輿情,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。任太守重,若涉淵冰,屬嗣服之雲初,其與民更始,可大赦天下,此詔。 嗣是駕還燕京,論功封賞,加哈喇哈孫爲太傅,答剌罕一作達爾罕。爲太保,並命答剌罕爲左丞相,牀兀兒、阿沙不花並平章政事。又以禿剌手縛阿忽臺,立功最大,封爲越王。哈喇哈孫謂祖宗舊制,必須皇室至親,方可加一字的褒封,禿剌系是疏屬,不得以一日功,廢萬世制。武宗不聽,禿剌未免挾恨,暗中進讒,說是安西謀變,哈喇哈孫亦嘗署名,自是武宗竟變了初志,將哈喇哈孫外調,令爲和林行省左丞相,仍兼太傅銜,陽似重他,陰實疏他。浸潤之譖,膚受之愬。一面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,授以金寶,以弟作子,煞是奇聞。在武宗的意思,還道是酬庸大典,格外厚施。既欲酬庸,不妨正名皇太弟,何必拘拘太子二字耶!又令廷臣議定祔廟位次,以順宗爲成宗兄,應列成宗右,乃將成宗神主,移置順宗下。成宗雖爲順宗弟,然成宗爲君時,順宗實爲之臣,兄弟不應易次,豈君臣獨可倒置耶?胡氏粹中謂如睿宗,裕宗,順宗,皆未嘗居天子位,但當祔食於所出之帝,其說最爲精當。配以故太子德壽母弘吉剌後,因後亦早逝,所以升祔,這且不必細表。 單說武宗初,頗欲創制顯庸,重儒尊道,所以即位未幾,即遣使闕里,祀孔子以太牢,且加號“大成至聖文宣王,”赦全國遵行孔教。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,用蒙古文譯《孝經》,進呈上覽,得旨嘉獎,並雲《孝經》一書,系《孔聖》微言,自王公至庶人,都應遵循,命中書省刻版模印,遍賜諸王大臣。宮廷內外,統因武宗尊崇聖教,有口皆碑。既而武宗坐享承平,漸眈荒逸,每日除聽朝外,好在宮中宴飲,招集一班妃嬪,恆歌酣舞,徹夜圖歡。酒色二字,最足盅人。有時與左右近臣,蹴踘擊球,作爲娛樂,於是媚子諧臣,陸續登進,都指揮使馬諸沙一作茂穆蘇。善角牴,伶官沙的一作錫迪。善吹笙,都令他平章政事。角牴吹笙的伎倆,豈關係國政乎?樂工犯法,刑部不得逮問;宦寺幹禁,詔旨輒加赦宥,而且封爵太盛,賞齎過隆,轉令朝廷名器,看得沒甚鄭重。 當時赤膽忠心的大臣,要算阿沙不花,見武宗舉動越制,容色日悴,即乘間進言道:“陛下居九重,所關甚大,乃惟流連麴櫱,暱近妃嬪,譬猶兩斧伐孤樹,必致顛仆。近見陛下顏色,大不如前,陛下即不自愛,獨不思祖宗付託,人民仰望,如何重要!難道可長此沉湎麼?”武宗聞言,倒也不甚介意,反和顏悅色道:“非卿不能爲此言,朕已知道了!卿且少坐,與朕同飲數杯。”大臣諫他飲酒,他恰邀與同飲,可謂歡伯。阿沙不花頓言謝道:“臣方欲陛下節飲,陛下乃命臣飲酒,是陛下不信臣言,乃有此諭,臣不敢奉詔!”武宗至此,方沈吟起來。左右見帝有不悅意,遂齊聲道:“古人說的主聖臣直,今陛下聖明,所以得此直臣,應爲陛下慶賀!”言未畢,都已黑壓壓的跪伏地上,接連是蓬蓬勃勃的磕頭聲。繪盡媚子諧臣的形狀。武宗不禁大喜,立命阿沙不花爲右丞相,行御史大夫事。阿沙不花道:“陛下納臣愚諫,臣方受職。”武宗道:“這個自然,卿可放心!” 阿沙不花叩謝而出,左右又奉爵勸酒。武宗道:“你等不聞直言麼?”左右道:“今日賀得直臣,應該歡飲,明日節飲未遲!”明日後,又有明日,世人因循貽誤,都以此言爲厲階。武宗道:“也好!”遂暢懷飲酒,直至酩酊大醉,方纔歸寢。越日,又將阿沙不花的言語,都撇在腦後了。可謂貴人善忘。 太子右諭德蕭,前曾徵爲陝西儒學提舉,固辭不至。武宗慕他盛名,召侍東宮,乃扶病至京師。入覲時,奉一奏摺,內錄尚書酒誥一篇,餘無他語。別開生面。嗣因武宗未嚴酒禁,謝病乞歸。或問故,蕭道:“朝廷尊孔,徒有虛名,以古禮論,東宮東面,師傅西面,此禮可行於今日麼?”遂還山。奉元人,操行純篤,教人必以小學爲基,所著有《三禮說》諸書。嗣病歿家中,賜諡貞獻。元代儒臣,多不足取,如蕭者亦不數覯,故特書之。過了數月,上都留守李璧,馳至燕都,入朝哭訴。由武宗問明原委,乃是西番僧強市民薪,民至李璧處訴狀,璧方坐堂審訊,那西僧率着徒黨,持梃入署,不分皁白,竟揪住璧發,按倒地上,捶撲交下。打到頭開目腫,還將他牽拽回去,閉入空室,甚至禁錮數日,方得脫歸。李璧氣憤填胸,遂入朝奏報武宗。武宗見他面有血痕,倒也勃然震怒,立命衛士偕璧北返,逮問西僧,械繫下獄。孰意隔了兩日,竟有赦旨到上都,令將西僧釋出。李璧不敢違命,只好遵行。 未幾僧徒龔柯等,與諸正合兒八剌妃爭道,亦將妃拉墮車下,拳足交加。侍從連忙救護,且與他說明擅毆王妃,應得重罪等語。龔柯毫不畏懼,反說是皇帝老子,也要受我等戒敕,區區王妃,毆她何妨!這王妃既遭毆辱,復聞譏詈,自然不肯干休,遣使奏聞。待了數日,並不見有影響。嗣至宣政院詳查,據院吏言,日前奉有詔敕,大略謂毆打西僧,罪應斷手,詈罵西僧,罪應斷舌,虧得皇太子入宮奏阻,始將詔敕收回等語。 看官閱此,總道武宗酒醉糊塗,所以有此亂命,其實宮禁裏面,還有一樁隱情,小子於二十六回中,曾敘及西僧勢焰,炙手可熱,爲元朝第一大弊。然在世祖成宗時代,西僧騷擾,只及民間,尚未敢侵入宮壷。至武宗嗣位,母后弘吉剌氏,建築一座興聖宮,規模宏敞得很,常延西僧入內,諷經建醮,禱佛祈福,不但日間在宮承值,連夜間也住宿宮中。那時妃嬪公主,及大臣妻女,統至興聖宮拜佛,與西僧混雜不清。這西僧多半淫狡,見了這般美婦,能不動心?漸漸的眉來眼去,同入密室,做那無恥勾當。漸被太后得知,也不去過問,自是色膽如天的西僧,越發肆無忌憚,公然與妃嬪公主等,luoti交歡,反造了一個美名,叫作“捨身大布施。”元宮婦女最喜入寺燒香,大約是羨慕此名。自從這美名流傳,宮中曠女甚多,哪一個不願結歡喜緣?只瞞着武宗一雙眼睛。武宗所嗜的是杯中物,所愛的是牀頭人,燈紅酒綠之辰,紙醉金迷之夕,反聽得滿座讚美西僧,譽不絕口,都受和尚佈施的好處。未免信以爲真。誰知已作元緒公。所以李璧被毆,及王妃被拉事,統擱置一邊,不願追究。就是太后弘吉剌氏,孀居寂寞,也被他惹起情腸,後來忍耐不住,也做出不尷不尬的事情來。爲下文伏脈。 武宗忽明忽暗,寬大爲心,今日敕造寺,明日敕施僧,後日敕開水陸大會,西僧教瓦班,善於獻諛,令他爲翰林學士承旨。並儒佛爲一塗,也是創聞。還有宦官李邦寧,年已衰邁,巧伺意旨,亦蒙寵眷。他的出身,是南宋宮內的小黃門,從瀛國公趙顯北行,得入元宮。世祖留他給事內廷,至此已歷事三朝,凡宮廷中之大小政事,他俱耳熟能詳。武宗嘉他練達,命爲江浙平章。邦寧辭道:“臣本閹腐餘生,蒙先朝赦宥,令承乏中涓,充役有年,愧未勝任。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,臣聞宰輔的責任,是佐天子治天下,奈何以刑餘寺人,充任此職,天下後世,豈不要議及聖躬麼!臣不敢聞命!”武宗大悅,擢他爲大司徒,兼左丞相銜,仍領太醫院事。邦寧竟頓首拜謝,受職而退。江浙平章,與大司徒同爲重任,辭彼受此,何異以羊易牛,此皆小人取悅慣技,武宗適墮其術耳。 越王禿剌自恃功高,嚐出入禁中,無所顧忌,就是對着武宗,亦惟以爾我相稱。武宗格外優容,不與計較,後來益加放肆,嘗語武宗道:“你的大位,虧我一人助成;倘若無我,今日阿難答早已正位,阿忽臺仍然柄政,哪個來奉承你呢?”武宗不禁色變,徐答道:“你也太囉唣了,下次不要再說!”禿剌尚欲有言,武宗已轉身入內,那時禿剌恨恨而去。 後來武宗駕幸涼亭,禿剌隨着,將乘舟,被禿剌阻住,語復不遜,自此武宗更滋猜忌。及宴萬歲山,禿剌侍飲。酒半酣,座中俱有醉意,禿剌復喧嚷道:“今日置酒高會,原是暢快得很,但不有我,哪有你等。你等曾亦憶及安西變事麼了”念茲在茲,可見小人難與圖功。武宗咈然道:“朕教你不要多言,你偏常自稱功。須知你的功績,我已酬賞過了,多說何爲?”禿剌聞言,將身立起,解了腰帶,向武宗面前擲來,並瞋目視武宗道:“你不過給我這物,我還你便罷!”言畢,大着步自去。 武宗憤甚,便語左右侍臣道:“這般無禮,還好容他麼?”侍臣統與禿剌有嫌,哪裏還肯勸解,自然答請拿問。當即命都指揮使馬諸沙等,率着衛士五百名,去拿禿剌。好在禿剌歸入邸中,沉沉的睡在牀上,任他加械置鎖,如扛豬一般,舁入殿中。迨至酒醒,由省臣鞫訊,尚是咆哮不服。省臣乃復奏禿剌不臣,陰圖構逆,宜速正典刑,有詔准奏,禿剌遂處斬,一道魂靈,馳入酆都,與阿忽臺等鬼魂,至閻王前對簿去了。小子有詩詠道: 褒封一字費評章,祖制由來是善防。 誰謂濫刑寧濫賞,須知恃寵易成狂! 欲知後事如何?且看下回分解。 ---------- 本回全爲武宗傳真,寫得武宗易喜易怒,若明若昧,看似尋常敘述,實於武宗一朝得失,俱櫽括其間,較讀《元史本紀》,明顯多矣。夫以武宗之名位論,敦不謂其當立,然吾謂其得之也易,故守之也難。嗣位未幾,即耽酒色,由是嬖倖臣,信淫僧,種種失政,雜沓而來。書所謂位不期驕,祿不期侈者,匪特人臣有然,人主殆尤甚焉!故武宗非一昏庸主,而其後偏似昏庸,爲君誠難矣哉!讀史者當知所鑑矣。
話說阿忽臺正準備抵抗時,突然看見一個威武的武士,才意識到自己不是對手。這人是誰呢?正是諸王禿剌。禿剌帶領衛兵去捉拿阿忽臺。阿忽臺害怕禿剌,卻不怕普通士兵,士兵上前,他把幾個人推開,想要趁機逃跑。可是禿剌親自出馬,把他攔住了。阿忽臺雖然知道自己不敵,也只能拼命抵抗。俗話說得好,棋差一着,就會處處被動;在武力對抗中,更不是他能比的。沒過幾回合,就被禿剌按在地上,衛兵用鐵鏈把他綁好。當時安西王阿難答以及諸王明裏帖木兒都沒有多大本事,早就被士兵抓住了。綁好之後,押送到上都,並且搜殺餘黨,同時禁錮了皇后。
事情初步平定後,諸王闊闊(也作庫庫)、牙忽都(也作呼圖)進去對愛育黎拔力八達說:“罪人已經被捕,宮中秩序已安,您該儘快登基,安定人心!”這話是奉承。愛育黎拔力八達說:“罪人祕密勾結後宮,破壞我家法秩序,所以我帶兵討伐,把他誅殺。我的本意並不是要專權奪位,覬覦皇位。懷寧王是我親哥哥,應該繼位,我已經派使者去北方迎接他。我們只需靜觀其變,等待哥哥登基即可。”
當時哈喇哈孫商議決定由八達監國,自己則統領衛兵,日夜居住在宮中以防變故,並命令李孟參贊政事。李孟對政務進行整頓,抑制權貴投機,很多大臣因此不滿。於是李孟嘆息道:“執政的大臣應當由天子親自任用,現在皇帝尚在路上,我還沒有見到天子,自然不敢輕易擔當大任。”於是他入宮堅決推辭,未被接受,最終辭官離開。
這時海山已經從青海出發,抵達和林。諸王貴族一同勸他即位。海山說:“我的母親和弟弟在燕京,等宗室親貴全部開會討論之後,才能決定。”於是暫時駐紮在和林,等待燕京消息。
此前,海山的母親弘吉剌氏曾請算命先生推算他和兒子的命運。算命先生說:“重光大荒落年會有災禍,‘旃蒙作噩’長久不息。”海山出生的年份是辛巳年,而愛育黎拔力八達出生的年份是乙酉年。根據《爾雅》記載,“大歲在辛”稱爲“重光”,在巳年稱“大荒落”;“在乙年”稱“旃蒙”,在酉年稱“作噩”。所以“重光大荒落”就是辛巳年,“旃蒙作噩”就是乙酉年。弘吉剌夫人一直記在心裏,於是派近臣朵耳前往和林,告訴海山:“你們兄弟都是我生的,本無親疏之分,但算命說命運長短不同,不可不深思!”
海山聽了,默不作聲。後來召見康裏脫脫,對他說:“我鎮守北方十年,年長且有功績,我認爲我應該繼位。我母親只是相信星命,這未必可信。如果我即位之後,順應天意,符合民心,即使有短暫的不足,也足以傳名萬世。怎能相信算命之說,辜負了祖宗重託!我認爲,這是當權大臣爲了阻止我繼位,故意製造混亂,設此陰謀來阻撓。你去探查情況,立刻回報我!”
康裏脫脫奉命前往燕京,報告弘吉剌夫人。弘吉剌夫人喫驚道:“命運長短雖有定數,我不過是爲他們長遠考慮,才提醒此事。他既然這樣說法,你就讓他立刻回來吧。”
於是派人把脫脫召回,又派阿沙不花前去迎接。恰逢海山率軍東進,途中遇到兩人。阿沙不花詳細敘述了安西王作亂的始末,以及太弟監國、諸王大臣擁戴他的意思。脫脫又以母親的話爲證。海山大喜,隨即與兩人一同進入上都,任命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,派他回去報告母親和弟弟。愛育黎拔力八達也帶着母親到上都,諸王大臣也隨行而來,當場議定,尊海山爲皇帝。
海山於是就在上都正式登基,追尊父親答剌麻八剌爲順宗皇帝,母親弘吉剌氏爲皇太后。隨後發佈詔書,宣佈赦免全國,廢除成宗皇后伯嶽吾氏,將其逐出京城,安置在東安州。又下令處死安西王阿難答、諸王明裏帖木兒,以及左丞相阿忽臺等人。因爲安西王與伯嶽吾後同住在宮中,嫂叔之間有不正當關係,明顯存在淫亂行爲,因此不立自己的兒子,反而想立皇叔,已嚴重敗壞皇室尊嚴,依照祖宗法度,罪不可赦,應令其自盡。詔書一出,伯嶽吾後毫無辦法,只能服毒自殺。這本是毫無樂趣的垂簾聽政,卻被她妄想破壞,導致身敗名裂,實在可嘆!
海山後來被稱爲武宗,所以我在他登基之後,都稱他爲武宗。
當時改年號爲“至大”,頒佈赦令。詔書寫道:
“我太祖以武功平定天下,世祖以文治安撫百姓,歷代君主相繼相承,國家延續綿長。我自先朝以來,鎮守北方十餘年,多次親率軍隊抵禦外敵,邊疆得以安寧。突然聽說皇帝駕崩,宗室諸王及勳貴元老在和林商議,都說我是世祖的孫子、裕宗正統的繼承人,以功績和賢德,應繼承帝位。我起初謙讓再三,其實早已暗中打算繼位。偏偏說謙讓再三,這正是中國文字中常見的欺騙手法,令人嘆息!回到上都後,宗親大臣又一再勸我即位。近來奸臣乘機謀反,多虧祖宗保佑,才得以平息。我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,奉太后之命,公正執法,平定叛亂。內亂已平,皇位不可長久虛懸,宗室血脈不可斷絕,衆臣共同勸請,心意堅定。我最終順應民意,於五月二十一日登基爲帝。雖然擔任重任,如同踏在冰上,但這是新君初登基之時,應與百姓共同開啓新的局面,特此大赦天下。”
隨後,皇帝返回燕京,論功行賞。加封哈喇哈孫爲太傅,答剌罕爲太保,並任命答剌罕爲左丞相,牀兀兒、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。又因禿剌親手擒獲阿忽臺,功勞最大,封爲越王。哈喇哈孫認爲祖宗舊制規定,只有皇室至親才能加“王”字封號,禿剌是疏遠的宗室,不應因一次功勞而打破千年舊制。武宗不聽,禿剌心中懷恨,暗中進讒言,說安西謀變時哈喇哈孫曾簽名,從此武宗改變了初衷,將哈喇哈孫外調,任命爲和林行省左丞相,仍保留太傅銜,表面看似重用,實則疏遠。這種細微的進讒,如同逐漸浸潤的毒害。武宗還立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,賜予金印玉冊,把弟弟當作兒子,真是奇聞。武宗原以爲這是酬庸大典,格外優待,其實他更應正名,稱“皇太弟”,何必拘泥於“太子”二字呢!又命大臣商議宗廟供奉順序,將順宗列爲成宗兄長,列入成宗右側,於是把成宗的神主移至順宗之下。成宗雖是順宗的弟弟,但成宗在位時,順宗只是臣子,兄弟之間不應倒置,難道君臣關係就可以反了?胡氏《粹中》認爲,睿宗、裕宗、順宗都沒有當過皇帝,應隨父親的廟號供奉,這個說法最爲恰當。至於配享的故太子德壽之母弘吉剌後,因爲她早逝,故被追加合祭,這裏不細說。
再說武宗即位之初,曾想改革制度,重視儒學,推崇道統。所以即位不久,就派使臣前往曲阜,用最隆重的禮節祭祀孔子,稱“大成至聖文宣王”,並下令全國遵行儒家教化。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將《孝經》翻譯成蒙古文進獻,皇帝大加讚賞,說《孝經》是孔子的精義,從王公到百姓,都應遵守,命中書省刻印發行,廣泛分發給諸王大臣。宮廷內外因武宗尊崇儒學,皆稱頌不已。
但後來武宗生活安定,逐漸沉溺於享樂,除了聽政外,喜歡在宮中飲酒作樂,聚集妃嬪,常常歌舞通宵,盡情歡愉。酒與色,最能迷惑人心。有時與身邊的近臣踢球、擊球取樂,於是寵信的宦官、伶人紛紛升遷。都指揮使馬諸沙(也作茂穆蘇)擅長角抵(一種摔跤),伶人沙(也作錫迪)擅長吹笙,都被任命爲平章政事。角抵、吹笙的技藝,與國家政事有何關聯?樂工犯法,刑部無法抓捕;宦官干政,皇帝下詔即行赦免。賞賜也過厚,爵位也過高,導致朝廷的名位顯得輕率,不再莊重。
當時真正忠誠的大臣,當屬阿沙不花。他看到武宗行爲失度,面色日漸憔悴,便趁機進言說:“陛下居於帝位,所牽涉的問題重大,卻只沉迷酒色,親近妃嬪,就好像用兩把斧頭砍一棵獨木樹,必定會傾倒倒塌。近來我看到陛下臉色,遠不如從前,陛下若不自愛,難道不考慮祖宗的託付和百姓的期盼嗎?怎麼可能一直沉溺下去呢?”武宗聽了,倒不以爲然,反而和顏悅色地說:“不是你不能說這種話,我已經知道了!你先坐一會兒,跟我喝幾杯。”大臣勸他戒酒,他卻邀他一起喝酒,真是個喜宴之主。阿沙不花立刻謝道:“我正想勸陛下節制飲酒,陛下卻讓我喝酒,這是不信任我的忠言,我不能奉命!”武宗這才沉思起來。大臣們見皇帝不高興,齊聲道:“古人說‘君明臣直’,如今陛下聖明,纔有這樣的直臣,應爲陛下慶祝!”話還沒說完,大臣們便紛紛跪下,接連不斷地磕頭,場面極其諂媚。武宗大喜,立即任命阿沙不花爲右丞相,兼行御史大夫。阿沙不花說:“陛下采納了我的忠言,我才能擔任此職。”武宗說:“當然,你可以安心。”阿沙不花叩謝後退出,衆臣又奉酒勸飲。武宗說:“你們沒聽說直言嗎?”左右答道:“今天賀得直臣,應盡情歡飲,明天再節制飲酒也不遲!”此後,又一天、又一天,世人因循拖延,把這句話當作禍根。武宗說:“也好!”便放縱飲酒,直至酩酊大醉,才入睡。第二天,又把阿沙不花的忠言全然忘記。真是貴人善忘。
太子右諭德蕭,此前曾任陝西儒學提舉,因身體有病,堅決推辭不就職。武宗仰慕他的名聲,召他入宮侍奉太子,他雖病體纏身,仍前往京城。入朝覲見時,呈上一份奏摺,內容只是抄錄了《尚書·酒誥》一篇,其餘無多言辭。後來因武宗對飲酒不加禁止,蕭謝病告退。有人問他原因,蕭說:“朝廷尊崇儒家,只是空名。從古禮看,太子東面而坐,師傅西面而立,這種禮制今天還能實行嗎?”於是辭官歸山。蕭遵循元代風俗,品行端正,教學注重基礎,著有《三禮說》等書。後來病逝於家中,被追諡爲“貞獻”。元代儒臣大多不稱職,像蕭這樣的人極爲罕見,故特別記載。
數月後,上都留守李璧急赴燕京,入朝哭訴。武宗查明原委,原來是西番僧人強行搶奪百姓柴薪,百姓到李璧處告狀。李璧正坐堂審理,那西僧率衆帶着兇器闖入官府,不分青紅皁白,揪住李璧頭髮,按倒在地,拳打腳踢。打得頭破血流,還把他拖走關進空屋,禁閉數日後才得以釋放。李璧憤怒不已,遂入朝上奏武宗。武宗見他臉上有血跡,勃然大怒,立即下令衛士隨同李璧北返,緝拿西僧,將其下獄。誰知兩天後,竟有赦令到達上都,下令釋放西僧。李璧不敢違抗,只好遵命放人。
不久,僧徒龔柯等人與正合兒八剌妃爭道,將妃拉下車,拳腳相加。侍從急忙救援,勸她別如此,指出毆打王妃應受重罰。龔柯毫不畏懼,反而說:“皇帝老子也要聽我訓導,區區王妃,打她有何不可!”王妃被羞辱,又聽人譏諷,自然不肯罷休,便派使者上奏。過了幾天,卻無任何回應。後來在宣政院查證,據院吏說,此前確實收到詔令,內容大致是:毆打西僧應斷手,辱罵西僧應斷舌,幸虧皇太子入宮勸阻,才收回詔令。
各位讀者看到這裏,或許會認爲武宗因喝酒而糊塗,纔會亂髮命令。其實宮內的情況更復雜,早在前文第二十六回中,已有描述西僧權勢膨脹,炙手可熱,是元朝的一大弊病。在世祖、成宗時期,西僧只騷擾民間,未曾進入宮中。到武宗即位後,母親弘吉剌氏修建了一座興聖宮,規模宏大,常邀請西僧入宮。西僧在宮中橫行無忌。武宗對這些也漸漸放縱起來,後來甚至讓西僧參與朝政。
越王禿剌自恃功高,常出入宮殿,肆無忌憚,對武宗也只以“你我”相稱。武宗對他格外寬容,不加責備。後來更放縱,曾對武宗說:“你的帝位,虧得我一個人幫助才成。若沒有我,如今阿難答早已稱王,阿忽臺仍在掌權,誰來奉承你呢?”武宗聽了臉色大變,緩緩回答:“你也太愛說了,下次不要再提!”禿剌還想再言,武宗已轉身進內,禿剌恨恨而去。
後來武宗駕臨涼亭,禿剌隨行,準備乘船,禿剌卻攔住,言語無禮,從此武宗更加多疑。在宴請於萬歲山時,禿剌陪飲。酒過半酣,衆人皆醉,禿剌再次喧譁說:“今天設宴,原是痛快,但沒有我,哪有你們的酒宴?你們可曾記得安西變事嗎?”這說明小人總是記着功勞,難與之共謀。武宗生氣地說:“我已叮囑你不要多言,你偏偏自誇功績。你的功勞,我已重賞,再多說何用?”禿剌聞言,站起身來,解開腰帶,當衆向武宗扔去,並怒目而視,轉身離開。
武宗心生憤恨,對身旁大臣說:“這種無禮,還能容忍嗎?”大臣們大多與禿剌有矛盾,哪裏還願勸解,紛紛請求抓他。當即下令由都指揮使馬諸沙等率領五百衛兵,去抓禿剌。好在禿剌正在家中睡覺,被強行戴上枷鎖,像扛豬一樣抬進宮殿。等到他酒醒,由官員審問,仍大聲不服。官員再奏報禿剌不忠,暗中圖謀叛亂,應立即處死。皇帝下詔批准,禿剌最終被處決,靈魂瞬間歸於陰間,與阿忽臺等人的鬼魂在閻羅前對簿公堂。
我作詩一首感嘆:
褒封一字費評章,祖制由來是善防。
誰謂濫刑寧濫賞,須知恃寵易成狂!
想知道後續如何,請看下回分解。
——本回全面真實地描寫了武宗的一生,寫得他容易喜怒,若明若昧。看似平實敘述,實則涵蓋了武宗一生的興衰得失,比讀《元史本紀》更清晰。從地位來看,武宗未必是應得之君,但我認爲他得位容易,守位就難了。即位不久即沉溺於酒色,寵信奸臣,信任佞僧,種種失政接連而來。古人說“地位不會自驕,俸祿不會自奢侈”,不僅臣子如此,君主更是如此。所以說,武宗並非一介昏庸之主,而其後逐漸變得昏庸,爲君之難,就在此處可見。讀史者應從中吸取教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