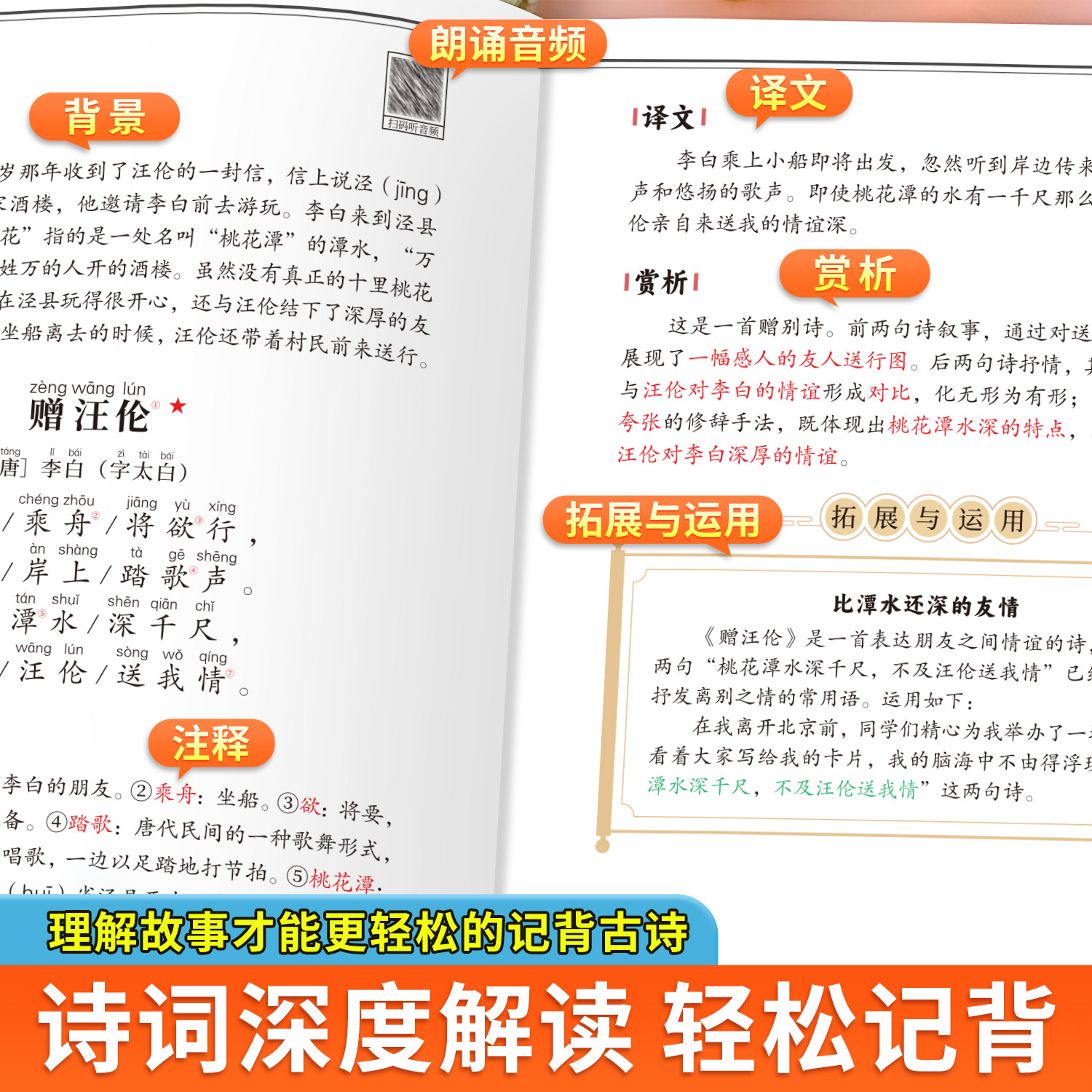卻說梁主信佛,太子綱獨信道教,嘗在玄圃中講論老莊。學士吳孜每入圃聽講,尚書令何敬容道:“昔西晉喪亂,禍源在祖尚玄虛,今東宮復蹈此轍,恐江南亦將致寇了。”這語頗爲太子所聞,很滋不悅。後來敬容妾弟費慧明,充導倉丞,夜盜官米,爲禁司所執,交領軍府懲辦。敬容貽書領軍將軍,代爲乞免。領軍將軍河東王蕭譽,爲太子綱猶子,見五十二回。當然與太子敘談,太子即囑令封書奏聞,梁主大怒,立將何敬容除名。敬容既去,朱異權勢益專,更得引用私人,攪亂朝政。散騎常侍賀琛不忍緘默,因上書論事,略雲: 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,明君不畜無益之臣,臣荷拔擢之恩,曾不能效一職,獻一言,此所以當食廢飱,中宵嘆息也。今特謹陳時事,具列於後,倘蒙聽覽,試加省鑑,如不允合,乞亮贛愚。其一事曰:今北邊稽服,戈甲解息,正是生聚教訓之時,而天下戶口減落,關外彌甚。郡不堪州之控總,縣不堪郡之裒削,更相呼擾,莫得治其政術,惟以應赴征斂爲事。小民輾轉流離,或依於大姓,或聚於屯封,蓋不獲已而竄亡,非樂之也。國 家於關外,賦稅蓋微,乃至年常租課,動致逋積,而民失安居,寧非牧守之過歟?東境戶口空虛,皆由使命煩數,駑困邑宰,則拱手聽其漁獵,桀黠長吏,又因之而爲貪殘,雖年降復業之詔,屢下蠲賦之恩,而民終不得反其居也。其二事曰:天下宰守,所以皆尚貪殘,罕有廉白者,實由風俗侈靡使然。夫食方丈於前,所甘一味,今之燕喜,相競誇豪,積果如山嶽,列餚同綺繡,露臺之產,不周一燕之資,加以歌姬盛畜,儛女盈庭,競尚奢淫,不問品制,凡爲吏牧民者,競事剝削,雖致資巨億,而罷歸以後,不支數年。率皆盡於燕飲之物,歌謳之具。所費等於邱山,爲歡止在俄頃,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,今所費之多,如復傅翼,增其搏噬,一何悖哉!其餘淫侈,日見滋甚,欲使人守廉隅,吏尚清白,安可得耶!今宜嚴爲禁制,導之以節儉,貶黜雕飾,糾奏浮華,使衆皆知變其耳目,改其好惡。蓋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,正雕流之弊,莫有過於儉樸者也。其三事曰: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,弘濟四海以爲心,不憚胼胝之勞,不辭癯瘦之苦,豈止日昃忘飢,夜分廢寢。至於百司,莫不奏事,上息責下之嫌,下無逼上之咎,斯實道邁百王,事絕千載。但斗筲之人,藻梲之子,既得伏奏帷扆,便欲詭競求進,不論國之大體,但務吹毛求疵,運挈瓶之智,僥分外之求,以深刻爲能,以繩逐爲務,跡雖似於奉公,事更成其威福,長弊增奸,實由於此。所願責其公平之效,黜其邪慝之心,則上安下謐,無僥倖之患矣! 其四事曰:曩昔征伐北境,帑藏空虛,今天下無事,而猶日不暇給者,何也?去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,事省則民養,費息則財聚。止五年之中,尚能無事,必能使國豐民阜,若積以歲月,成效愈巨,斯乃范蠡滅吳之術,管仲霸齊之由。今應內省職掌,各簡所部,或十省其五,成三除其一,至國容戎備,在昔應多,在今宜少,凡四方屯傳邸治,或舊有,或無益,有所宜除除之,有所宜減減之,興造有非急者,徵求有可緩者,皆宜停省,以蓄財而息民,蓄其財者,正所以大用之也,息其民者,正所以大役之也。若擾其民而欲求生聚,耗其財而徒務賦斂,則奸詐盜竊,日出不已,何以語富強,圖遠大乎?伏思自普通以來,二十餘年,刑役薦起,民力雕流,今魏氏和親,疆埸無警,不於此時大息四民,使之殷阜,減省國費,使之儲峙,一旦異境有虞,關河可掃,則國弊而民疲,事至方圖,恐無及矣!臣心所謂危,罔知忌諱,謹昧死上聞! 梁主衍覽書,不禁大怒,立召侍臣至前,口授教書,令他照錄,大旨是詰責賀琛,令他據實指陳,不得徒託空言。第一事謂牧守貪殘,應指出某官某吏,以便黜逐。第二事謂風俗侈靡,不便一一嚴禁,自增苛擾。朕常思本身作則,絕房室三十餘年,不飲酒,不好音,雕飾各物,從未入宮。宗廟牲牢,久未宰殺,朝廷會同,只備蔬菜,且未嘗奏樂。朕三更即起理事,每至日昃,日常一食,昔腰十圍,今裁二尺,勤儉如許,不得謂非淳素。捨本逐末,無益於事。第三事謂百司幹進,誰爲詭競?誰爲吹毛求疵?誰爲深刻繩逐?若不令奏事,專委一人,與秦二世寵信趙高,漢元后付託王莽,亦復何異?第四事謂省事息費,究竟何事宜省?何事宜息?國容戎備,如何減省?屯傳邸治,如何裁併?何處興造非急,何處徵求可緩?宜條具以聞,不得空作漫語,徒沽直名。這道敕文,頒給賀琛,琛不禁畏縮,未敢復奏,但申表謝過罷了。原來是銀樣鑞槍頭。 大同十二年三月,梁主衍又幸同泰寺,講三慧經,差不多過了一月,方纔罷講。再設法會,大赦天下,改元中大同。是夜同泰寺竟肇火災,毀去浮圖,梁主嘆道:“這便佛經上叫作魔劫呢!”浮圖成災,並非魔劫,似你這般佞佛,卻是要墮入魔劫了!遂令重造浮圖十二層,格外崇閎,需工甚巨,經年未成。梁主衍年逾八十,雖精神尚可支持,終究是老態龍鍾,不勝繁頤。再加平時覽誦佛經,時思修寂,尤覺得耄期倦勤,厭聞政治。 是時儲嗣雖定,諸子未免不平,因爲梁主不立嫡孫,但立庶子,大家資格相等,沒一個不覬覦神器,猜忌東宮。邵陵王綸,系梁主第六子,性最浮躁,喜怒無常,車服嘗僭擬乘輿,遊行無度。梁主屢戒不悛,曾將他錮置獄中,免官削爵,已而仍復舊封,命爲揚州刺史,縱肆如故。遣人就市購物,不給價值,商民怨聲載道,甚至罷市。府丞何智通具狀上聞,綸竟遣人刺殺智通。梁主乃將綸召回,鎖禁第舍,免爲庶人。過了數月,又賜復封爵,何溺愛乃爾!授丹陽尹。綸恃寵生驕,妄思奪儲,太子綱當然嫉視,請出綸爲南徐州刺史,有詔依議。還有梁主第五予廬陵王續,出鎮荊州,第七子湘東王繹,出鎮江州,第八子武陵王紀,出鎮益州,皆權侔人主,威福自專。惟次子豫章王綜,已死北朝,四子南康王績,長孫豫章王歡,俱已去世,免爲東宮敵手。但太子綱終不自安,常挑選精卒,爲自衛計。 梁主衍未察暗潮,反因舍嫡立庶的情由,未免內愧,所以待遇昭明太子諸男,不亞諸子。河東王譽得爲湘州刺史,岳陽王詧,亦授雍州刺史。鑞見梁主年老,朝多秕政,也不免隱蓄雄心,豫先戒備。自思襄陽形勝,爲梁業開基地,正好作爲根據,遂聚財下士,招募健卒數千人,環列帳下。一面究心政事,拊循士民,轄境稱治。未幾廬陵王續,病歿任所,調江東王繹繼任。繹喜得要地,入閤歡躍,靴履爲穿。 梁主怎知諸子用意,總道是孝子賢孫,不復加憂,整日裏唸佛誦經,蹉跎歲月。中大同二年,又復捨身同泰寺,羣臣出金奉贖,如前二次故例。滿望佛光普照,天子萬年,哪知禍爲福倚,福爲禍伏,平白地得了河南,收降了一個東魏叛臣,遂鬧得翻天覆地,大好江南,要變做銅駝荊棘了。直呼下文。 且說東魏大丞相高歡,自邙山戰後,按兵不動,休養了兩三年。東魏主善見覆改元武定。嗣聞柔然與西魏連兵,將來犯境,乃亟令高歡爲備。歡仍執前策,決與柔然續行修好,遣行臺郎中杜弼爲使,北詣柔然,申議和親,願爲世子澄求婚。澄已有妻有妾,還要求什麼婚!頭兵可汗道:“高王若須自娶,願將愛女遣嫁。”還要悖謬。杜弼歸報高歡,歡年已五十,自思死多活少,不堪再偶柔然公主,因此猶豫未決。何必猶豫,將來替汝效勞,大有人在。事爲婁妃所聞,遂白歡道:“爲國家計,不妨從權,王無庸多疑!”歡半晌才道:“我娶番女,豈不要委屈賢妃?”婁妃道:“國事爲大,家事爲輕,枉尺直尋,何惜一妾!”歡一笑而罷。已而世子澄與太傅尉景,俱勸歡迎納柔然公主,歡乃使慕容儼爲納采使,迎女南來。 歡出迎下館,但見柔然僕從,無論男女,統皆控騎而至,就是這位新嫁娘,亦坐下一匹紅鬃馬,身服行裝,腰佩弓矢,落落大方,毫無羞澀態度。最後隨着一位番官,也是雄赳赳的少年,與新嫁娘面龐相似。歡又驚又喜,問明慕容儼,乃知送親的隨員,便是女弟禿突佳。當下彼此接見,問訊已畢,始引還晉陽城。歡妾大爾朱氏等,也出城相迎,一擁而歸。柔然公主素善騎射,在途見鵾鳥飛翔,便在佩囊中取出弓矢,一發即中,鵾隨箭落。大爾朱氏亦不禁技癢,由從人手中取過了弓箭,亦斜射飛鳥,應弦而落。既有此技,何不前時射死高歡,爲主復仇!歡大喜道:“我得此二婦,並能擊賊,豈非快事!”說着,便縱轡入城。 到了府舍,與柔然公主行結婚禮,婁妃果避出正室,令柔然公主安居。歡感激異常,尋至別室,得見婁妃,不由的五體投地,向妻拜謝。婁妃慌忙答禮,且笑且語道:“男兒膝下有千金,奈何向妾下跪!況番國公主,有所察覺,反覺不美,王儘管自去,與新人作交頸歡,不必多來顧妾了!”歡乃起身去訖。是夕老夫少妻,共效于飛,不必絮述,惟大爾朱氏器量褊窄,未及婁妃的大度,她情願出家爲尼。歡特爲建築佛寺,俾她靜修。 禿突佳傳述父命,謂待見外孫,然後返國,因此留居晉陽。看官!試想這高歡年經半百,精力漸衰,況他是好酒漁色,寵妾盈庭,平時已耗盡脂膏,怎能枯楊生稊,一索得男!柔然公主望兒心急,每夕嬲歡不休,累得歡形容憔悴,疾病纏身。有時入宿射堂,暫期休養,偏禿突佳硬來逼迫,定要歡去陪伴乃姊,歡稍稍推諉,禿突佳即發惡言。可憐歡無從擺脫,沒奈何往就公主,力疾從事,峨眉伐性,實覺難支。歡乃想出一法,只說要出攻西魏,督軍經行。肉戰不如兵戰。 先是西魏幷州刺史王思政居守恆農,兼鎮玉璧,嗣受調爲荊州刺史,舉韋孝寬爲代。孝寬蒞任後,聞高歡率軍西來,即至玉璧扼守。歡至玉璧城下,晝夜圍攻,孝寬隨機抵禦,無懈可乘。城中無水,仰給汾河,歡堵住水道,並就城南筑起土山,擬乘高扒城。城上有二樓,孝寬縛木相接,高出土山,居上臨下,使不得逞。歡憤語守兵道:“雖爾縛樓至天,我自有法取爾。”因鑿地爲十道,穿入城中。孝寬四面掘塹,令戰士屯守塹上,見有地道穿入,便塞柴投火,用皮排吹,地道變成火窟,掘地諸人,悉數焦爛。歡又改用攻車撞城,孝寬縫布爲幔,懸空遮護,車不能壞。歡命兵士各執竹竿,上縛松麻,灌油加火,一面焚布,一面燒樓,孝寬用長鉤鉤竿,鉤上有刃,得割松麻,竿仍無用。歡再穿地爲二十道,中施樑柱,縱火延燒,柱折城崩。孝寬積木以待,見有崩陷,立即豎柵,歡軍仍不得入。城外攻具已窮,城內守備,卻還有餘。 孝寬更夜出奇兵,奪據土山。 歡知不能拔,乃使參軍祖珽,呼孝寬道:“君獨守孤城,終難瓦全,不如早降爲是!”孝寬厲聲答道:“我城池嚴固,兵多糧足,足支數年,且孝寬是關西男子,怎肯自作降將軍!”珽復語守卒道:“韋城主受彼榮祿,或當與城存亡,汝等軍民,何苦隨死?”守卒俱搖首不答。珽復射入賞格,謂能斬城主出降,拜太尉,封郡公,賞帛萬匹。孝寬手題書背,返射城外,謂能斬高歡,准此賞格。歡苦攻至五十日,始終不能得手,士卒戰死病死,約計七萬人,共爲一冢。大衆多垂頭喪氣,歡亦舊病復作,入夜有大星墜歡營中,營兵大譁,乃解圍引還。歡悉衆攻一孤城,終不能下,所謂強弩之末,勢不能穿魯縞。當時遠近訛傳,謂歡已被孝寬射死。西魏又申行敕令道:“勁弩一發,凶身自殞。”歡也有所聞,勉坐廳上,引見諸貴。大司馬斛律金爲敕勒部人,歡使作敕勒歌,歌雲:“敕勒川,陰山下,天似穹廬,籠罩四野。天蒼蒼,夜茫茫,風吹草低見牛羊。”斛律金爲首倡,歡依聲作和,語帶嗚咽,甚至淚下。死機已兆。自此病益沉重,好容易延過殘冬,次年爲武定五年,元旦日蝕,歡已不能起牀,慨然嘆道:“日蝕恐應在我身,我死亦無恨了!”日蝕乃天道之常,幹卿甚事!遂命次子高洋,往鎮鄴郡,召世子澄返晉陽。 澄入問父疾,歡囑他後事,澄獨以河南爲憂。歡說道:“汝非憂侯景叛亂麼?”澄應聲稱是。歡又道:“我已早爲汝算定了,景在河南十四年,飛揚跋扈,只我尚能駕馭,汝等原不能制景,我死後,且祕不發喪,庫狄幹、斛律金,性皆道直,終不負汝。可朱渾元、劉豐生,遠來投我,當無異心。韓軌少戇,不宜苛求。彭樂輕躁,應加防護。將來能敵侯景,只有慕容紹宗一人,我未嘗授彼大官,特留以待汝,汝宜厚加殊禮,委彼經略,侯景雖狡,想亦無能爲了。”說至此,喉中有痰壅起,喘不成聲,好一歇始覺稍平,乃復囑澄道:“段孝先即段韶字。忠亮仁厚,智勇兼全,如有軍旅大事,儘可與他商議,當不致誤。”是夕遂歿,年五十二。 澄遵遺命,不發喪訃,但詭爲歡書,召景詣晉陽。景右足偏短,騎射非長,獨多謀算,諸將如高敖曹、彭樂等,皆爲景所輕視。嘗向歡陳請,願得兵三萬,橫行天下,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,令作太平寺主,歡因使景統兵十萬,zhuanzhi河南。景又嘗藐視高澄,私語司馬子如道:“高王尚在,我未敢有異心,若高王已沒,卻不願與鮮卑小兒共事。”子如忙用手掩住景口,令勿多言。景復與歡約,謂自己握兵在外,須防詐謀,此後賜書,請加微點,歡從景言,書中必加點以作暗號。高澄卻未知此約,作書召景,並不加點,景遂辭不就徵。且密遣人至晉陽,偵歡病狀。 旋接密報,晉陽事盡歸高澄主持,料知歡必不起,乃決意叛去,通書西魏,願舉河南降附。西魏授景爲太傅,領河南大行臺,封上谷公。景遂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,襄州刺史李密,廣州刺史暴顯等,潛遣兵士二百人,夜襲西兗州,被刺史邢子才探悉,一律掩獲,因移檄東方諸州,各令嚴防。高澄即派司空韓軌,督兵討景。 景恐關、陝一路,爲軌所斷,不如南向投梁,較無阻礙,乃遣郎中丁和,奉表至梁。內言臣景與高澄有隙,願舉函谷以東,瑕邱以西,如豫、廣、潁、荊、襄、兗、南兗、濟、東豫、洛陽、北荊、北揚等十三州內附,所有青、徐數州,但須折簡,即可使服。齊、宋一平,徐事燕、趙,混一天下,便在此舉云云。忽降西魏,忽附南朝,景之狡猾已可想見。梁主衍接閱景表,因召羣臣廷議,尚書僕射謝舉進諫道:“近來與東魏通和,邊境無事,若納彼叛臣,臣竊以爲未可!”梁主怫然道:“機會難得,怎得膠柱鼓瑟?”羣臣多贊成舉議,請勿納景。獨有一人鼓掌道:“天與不取,反受其咎;況陛下吉夢徵祥,臣曾料是混一的預兆,今言果驗,奈何勿納!”梁主亦欣然道:“誠如卿言,朕所以擬納侯景呢。”小子有詩嘆道: 豎牛入夢叔孫亡,故事曾從經傳詳; 盡說春秋成答問,如何迷幻自招殃!梁武曾作春秋答問,見《梁書本紀》。 究竟梁主曾夢何事,與梁主詳夢,及勸納侯景,又爲何人?俟小子下回再詳。 ------------- 賀琛上書言事,臚陳四則,未嘗無理。梁主衍護短矜長,頒敕詰責,昏髦情形,已可概見。然讀其敕文,猶令琛指實具陳,琛少振即餒,仍作寒蟬,主不明,則臣不能伸其直,於琛何尤焉!惟梁主信佛過甚,教子無方,琛上書時,亦未聞提及,捨本逐末,皮相虛談,繩以國家大體,琛固未足知此也。高歡年已五十,尚娶蠕蠕公主,老猶漁色,不死何爲?玉璧之圍,五旬不下,雖由韋孝寬之善守,亦由高歡之精神不濟,未能振作軍心。將帥疲敝,而望士卒之振奮,不可得也。及歸死晉陽,猶能智料侯景,以慕容紹宗爲囑,工心計於生前,貽智謀於身後,此其所以爲亂世之雄也歟!
梁武帝信仰佛教,而太子蕭綱卻信奉道教,曾多次在玄圃園中講解老莊之學。學士吳孜每次去園中聽講,尚書令何敬容便說:“昔日西晉滅亡,禍亂的根源在於崇尚虛無玄妙之學,如今東宮又重蹈覆轍,恐怕江南也將因此遭到戰亂。”這話被太子聽到了,很是不高興。後來,何敬容的妾弟費慧明擔任導倉丞,夜裏偷盜官府糧食,被官府查辦,交由領軍府處理。何敬容便寫信給領軍將軍,請求爲他求情。領軍將軍是太子的堂侄蕭譽,兩人關係密切,太子便囑咐他將信轉呈給皇帝。梁武帝得知後極爲憤怒,立刻將何敬容罷免職務。何敬容被罷官後,朱異的權勢更加強大,還引薦私人,進一步擾亂朝政。散騎常侍賀琛心懷憤懣,於是上書直言時弊,內容大致如下:
我聽說慈愛的父親不會寵愛無用的兒子,賢明的君主不會任用無益的臣子。我承蒙提拔,卻未能盡到一個臣子應盡的職責,更沒有提出一條有用的意見,因此常常食而不飽,半夜嘆息。今天我謹將當前時政的四個問題列出來,懇請陛下閱覽,加以體察。如果意見不被採納,也請明察我的苦衷。
第一件事:如今北方邊境已歸順,兵器停用,正是人們安居樂業、休養生息的好時機,然而全國戶口不斷減少,尤其是邊遠地區更爲嚴重。郡縣無法承受州府的管轄,縣令也無法承受郡級的過度攤派,地方之間相互掣肘,難以施展政令,只知應付徵稅。百姓輾轉流離,有的投靠大戶人家,有的聚集在軍屯或封地裏,都是迫不得已的逃亡,並非他們本意。國家在邊遠地區徵收的賦稅其實很少,卻常常出現拖欠,百姓沒有安穩的生活,這難道不是地方官員失職的表現嗎?東邊邊境人口稀少,是由於官府派遣的使臣過多,地方官吏疲於應付,於是聽任他們盤剝百姓,一些惡行貪婪的官員趁機作惡。即使朝廷反覆下詔恢復農耕、減免賦稅,百姓也始終無法迴歸故土。
第二件事:全國的地方官員大多貪污殘暴,很少有廉潔清正的,這其實是社會風氣奢侈浮華爲因。如今人們在宴會上,喫一碗飯,只追求其中一道菜的精緻,爭相炫耀奢華。堆積的水果如山峯,擺放的菜餚像錦繡,甚至屋內裝飾的物品,也貴重到足以買下一隻野鳥。更兼蓄養歌女舞姬,廳堂盈滿,爭相追求奢侈放縱,不顧禮法規範。凡爲官者,都以此爲務,盤剝百姓。雖能積累鉅額財富,但一旦退休,幾年之內就因宴飲和音樂器物的開銷而耗盡家產。這些花費如同堆積如山,快樂只維持片刻,事後反而怨恨自己當初所得太少,現在花費太多,若再繼續這樣,豈非更加貪婪暴虐?而這種奢侈之風每天都在加劇。若想讓百姓守廉節、官吏清白,又怎能實現呢?應嚴格禁止奢侈,引導人們崇尚節儉,貶抑浮華裝飾,追查浮誇行爲,使大家轉變自己的喜好,迴歸樸素本性。治理國家,必須以淳樸爲根本,糾正奢侈的風氣,沒有比提倡節儉更重要的了。
第三件事:聖上肩負着拯救天下蒼生的重任,心懷安定四海的抱負,不害怕辛勞,不嫌棄清貧,不只是每天忙到日落才能休息,夜裏也不休息。百官爭相上奏事務,上不埋怨下級,下也不逼迫上級,這確實是超越歷代的治世之道。但那些品行低劣、地位卑賤的小人,一旦進入朝廷,便想通過吹毛求疵、曲解政令來謀求升遷,不顧國家大局,只圖個人得利,以苛刻苛求爲能,以追查小過爲務。這些行爲看上去看似忠於職守,實則助長了權勢和貪腐,是造成腐敗和弊端的根源。我懇請皇上嚴查這些官員的公平表現,罷黜那些邪惡自私的人心,這樣上下才會安寧,國家才能免於禍患。
第四件事:過去征伐北方時,國庫空虛,如今天下太平,卻依然財政緊張,這是爲什麼?過去國家腐敗混亂,就應該精簡事務,節省開支,事務減少,百姓才能得到休養;開支減少,財富才能積聚。在過去五年中,尚且能維持不亂,若能繼續堅持下去,國力必將強盛,百姓富足。這正是范蠡滅吳、管仲稱霸的策略。現在應當整頓各部職事,精簡機構,比如每十個部門裁去五個,每三個中裁去一個。至於國家軍事防禦,從前應多,如今應少。各地駐軍、驛站、治所,若有無用的,就應裁撤;若有冗餘的,就應減少。凡屬非緊急的興建工程和可以延遲的徵稅事項,都應暫停,以積攢財富、休養生息。只有這樣,國家才能積蓄財富,才能更大規模地用於國事,讓百姓得以休養,才能真正實現大用與大役。若擾民徵稅、耗費國財只圖賦斂,必將導致盜賊滋生,怎麼能談國家富強與遠大圖謀呢?我回憶自普通年間以來二十多年間,刑罰和勞役不斷,百姓民力已嚴重受損。如今魏國與我朝和親,邊境無戰事,正是應趁此機會恢復百姓生計,讓他們富裕起來,同時減少開支,儲備財物。一旦外患來襲,邊關可以迅速平定。若此時不整頓,等戰事爆發時再想應對,恐怕已無及矣!我心中所憂,雖無忌諱,謹冒死上書!
梁武帝讀完這封奏書,極爲憤怒,立刻召見近臣,親口命他們將這封奏章抄錄,主要內容是質問賀琛,要求他實話實說,不得空談。第一件事要指出具體官員和地方官吏,以便罷免。第二件事批評風俗奢侈,不可一一嚴查,以免造成過度擾民。我常以身作則,三十年不娶妻不飲酒,不喜好音樂,不追求華麗裝飾,從未進入宮室。宗廟祭祀,多年未曾宰殺牲畜,朝廷會面,只備蔬菜,從不奏樂。我每天三更起身處理政事,常常到日落才休息,每天只喫一餐,過去腰圍十圍,現在只剩二尺。勤儉如此,怎能說我不節儉呢?他捨本逐末,毫無實際意義。
第三件事批評百官爭相進言,誰在虛張聲勢?誰在吹毛求疵?誰在苛責他人?若不設立專人負責奏事,不將這些小事歸於一人,豈不如同秦二世寵信趙高,漢元后託付王莽一樣?第四件事問:到底哪些事務該精簡?哪些開銷該減少?軍隊和邊境防禦應如何削減?駐地驛站應如何裁撤?哪些工程非緊急可停?哪些徵稅可推遲?請詳細列出,切莫空談,勿圖虛名。
這道敕令被下達給賀琛,賀琛嚇得渾身發抖,不敢再上書,只上表謝罪。這其實是“銀樣鑞槍頭”——外表華麗,內裏空虛,毫無實質。
大同十二年三月,梁武帝又到同泰寺講《三慧經》,差不多過了一個月,才結束講經。接着再次舉行法會,大赦天下,並改元爲“中大同”。當晚,同泰寺突然發生火災,燒燬了佛塔。梁武帝感嘆道:“這就是佛經裏所謂的‘魔劫’!”其實這並非真正的魔劫,而是他過於迷信佛教,實則是自招災禍,必將墜入魔障。於是下令重建佛塔,規模擴大到十二層,工程浩大,耗費巨資,多年才完成。
梁武帝年過八十,雖然精神尚可,但已顯老態,體力不支,日漸疲憊。平時常誦經修道,尤其對晚年生活厭倦政事,對政治越來越反感。
這時儲君雖已確定,諸子之間卻互相不服,因爲梁武帝不立嫡系子孫,僅立庶出子弟,諸子地位平等,人人都想爭奪皇位,對太子心生猜忌。邵陵王蕭綸是梁武帝第六個兒子,性情浮躁,喜怒無常,曾多次僭越皇帝儀仗,遊蕩無度。梁武帝屢次告誡,他也始終不改,曾一度把他關進監獄,免去官職,削去爵位,後來又恢復原職,任命爲揚州刺史,依舊放縱不法。派人去市場購物,不給合理價格,百姓怨聲載道,甚至罷市。府丞何智通上報朝廷,蕭綸竟派人暗殺何智通。梁武帝因此將蕭綸召回,關入府中,降爲平民。數月後又賜其復封,寵溺有加。任命他爲丹陽尹。蕭綸倚仗寵愛,日漸驕橫,企圖奪走太子之位,太子蕭綱自然嫉恨,請求將他外調爲南徐州刺史,朝廷批准。其他兒子也紛紛出鎮:第五子廬陵王蕭續出鎮荊州,第七子湘東王蕭繹出鎮江州,第八子武陵王蕭紀出鎮益州,均掌握軍權,權勢與皇帝相當。只有第二子豫章王蕭綜已死於北朝,第四子南康王蕭績,長孫豫章王蕭歡,也早已去世,無從與太子相抗衡。然而太子蕭綱始終不安心,常挑選精銳士兵自衛。
梁武帝未能察覺內部動盪,反而因爲不立嫡子而內心愧疚,因此對諸皇子們也待遇與諸子一樣。河東王蕭譽被任命爲湘州刺史,岳陽王蕭詧也被任命爲雍州刺史。面對朝政混亂,梁武帝也暗自警覺,開始蓄謀自保。他認爲襄陽地勢重要,是梁朝經營的根基,便聚集錢財、招攬人才,招募數千精兵,環繞帳下。同時認真思考政務,安撫百姓,境內治理稱得上良好。不久廬陵王蕭續在任上病亡,朝廷改由江陵王蕭繹接任。蕭繹得到要地,極爲高興,入宮歡躍,連鞋子都踩破了。
梁武帝根本不知諸子的野心,仍以爲他們只是孝順賢明的子孫,不加憂慮,整天誦經唸佛,虛度光陰。中大同二年,他又一次捨身同泰寺,羣臣出錢贖他,和前兩次一樣。原本希望藉此得福,祈求萬年長治,誰知禍從福來,福轉爲禍,竟然在無意識中失去了河南地區,收降了一個東魏叛將,導致局勢驟變,原本繁榮的江南,頃刻間陷入戰火,變成一片廢墟。
再說東魏大丞相高歡,在邙山之戰後,便停止進攻,休養生息兩年多。東魏國主高善見改元“武定”。後聽說柔然與西魏聯合進犯,便急令高歡備戰。高歡仍堅持先前策略,決定與柔然和親,派行臺郎中杜弼出使北柔然,提議結盟,並請求爲世子高澄迎娶柔然公主。高澄已有妻妾,又何須再娶?柔然可汗說:“高王若要娶,我願把愛女嫁給他。”這更加荒唐。杜弼返回後報告此事,高歡便同意。後來,高歡派高澄統兵十萬,前往河南。高澄曾輕視高歡,私下對司馬子如說:“高王還在,我還沒敢有異心;若高王死了,我不願與這些鮮卑人共事。”司馬子如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,讓他不要再說。高澄還與高歡約定,自己在外掌兵,必須防範陰謀,今後寫信給高歡,必須在信中加點作爲暗號。而高澄並不知道這一約定,寫信召高景時,未加暗號,高景遂推辭不去。同時,祕密派人前往晉陽,探查高歡的病情。
不久,得到密報:晉陽由高澄全權掌控,料定高歡必死,於是決定起兵反叛,寫信投靠西魏,表示願意歸附。西魏封他爲太傅,領河南大行臺,封上谷公。高景於是誘捕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廣州刺史暴顯等人,祕密派遣二百名士兵,夜間襲擊西兗州,被刺史邢子才察覺,全部抓獲。隨即發佈通告,要求各州嚴防。高澄立即派司空韓軌領兵討伐。
高景害怕關中、陝西被韓軌切斷,不如轉而南投梁朝,阻力更小,於是派郎中丁和向梁朝遞交表文。表中寫道:“臣高景與高澄有矛盾,願將函谷關以東,瑕丘以西,包括豫、廣、潁、荊、襄、兗、南兗、濟、東豫、洛陽、北荊、北揚等十三州歸附大梁,青、徐二州則只需發一紙文書,即可歸順。若齊、宋平定,便可向燕、趙擴張,統一天下。”可見高景反覆無常、狡猾奸詐。梁武帝看到高景的表文,便召集羣臣商議。尚書僕射謝舉進諫說:“近來我們與東魏和親,邊境安寧,若接納這位叛臣,我私下認爲不可。”梁武帝勃然大怒:“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,怎能死守舊法?”衆臣大多贊同接納,唯有一人拍手叫好:“天賜良機,不取反受其害;況且我曾預感陛下將有徵伐大業,如今果然應驗,何故拒絕?”梁武帝聽了也非常高興:“確實如此,我正是打算接納侯景。”後人有詩嘆曰:
豎牛入夢叔孫亡,故事曾從經傳詳;
盡說春秋成答問,如何迷幻自招殃!
梁武帝究竟夢見了什麼?他與大臣詳細討論過此事,爲何又決定接納侯景?這些細節,留待下回詳述。
賀琛上書言事,條理清晰,四個問題並非無理。梁武帝卻護短自大,發下敕令質問,昏庸無能的統治局面已可見一斑。然而讀其敕文,仍要求賀琛詳細指出具體事實,結果賀琛一看到就怯懦退縮,不再直言。主上不明,臣子怎能伸張正義?對此,賀琛有何可怨呢?只是梁武帝過於迷信佛教,對子女教育無方,賀琛上書時並未提及,他所言皆浮於表面,只談表面現象,未能觸及國家根本。如果以國家大勢爲重,賀琛也實在不配理解。高歡年已五十,仍娶柔然公主,老來仍沉迷男女之事,不死何爲?玉璧之戰,五十天未能攻下,雖因韋孝寬防守得力,但主要還是高歡體弱多病,軍心渙散所致。將帥疲敝,指望士卒奮勇,終是徒勞。等到最終病逝於晉陽,仍能預見侯景之亂,命人善待慕容紹宗,將計謀提前安排於身後,這是他作爲亂世梟雄的智慧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