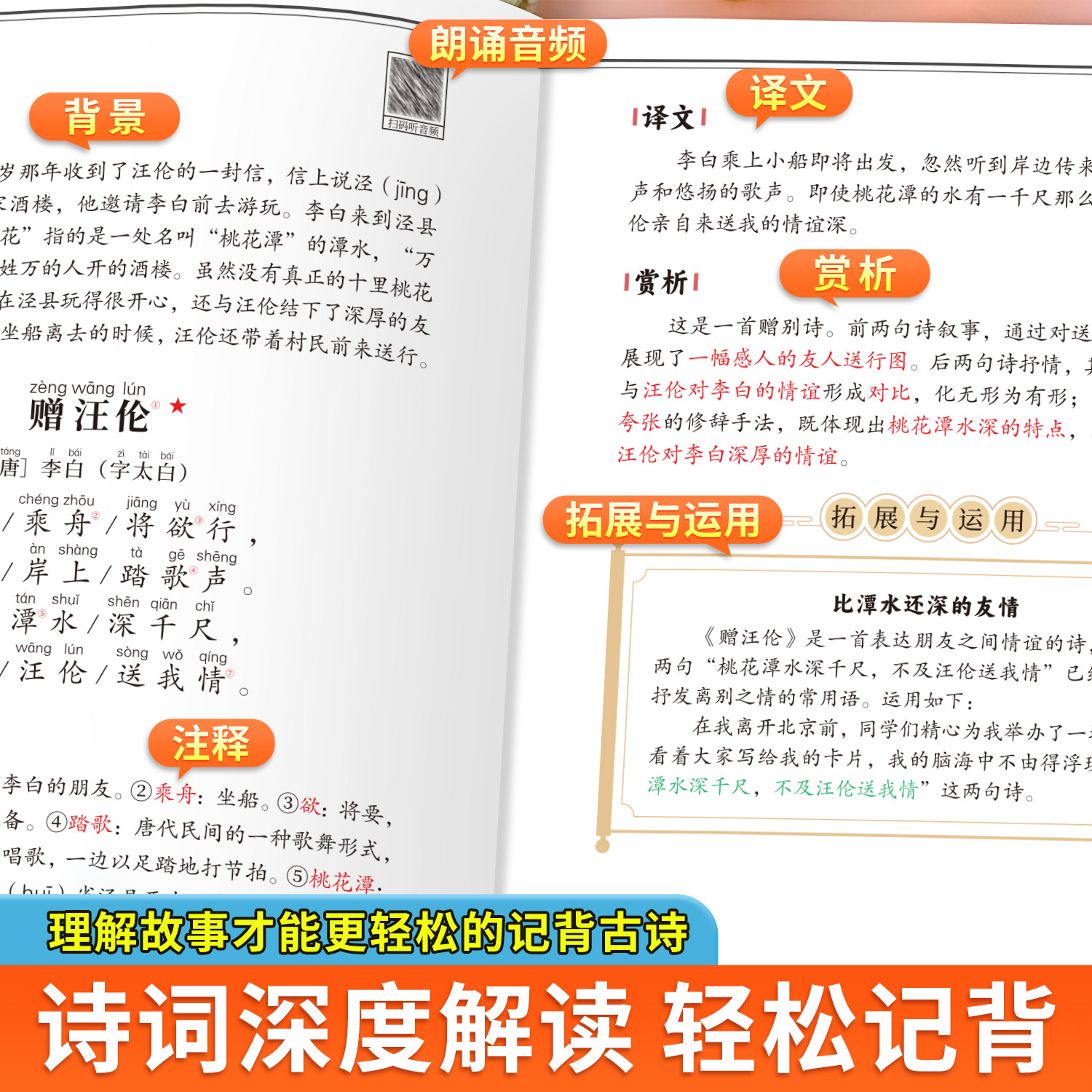却说梁主信佛,太子纲独信道教,尝在玄圃中讲论老庄。学士吴孜每入圃听讲,尚书令何敬容道:“昔西晋丧乱,祸源在祖尚玄虚,今东宫复蹈此辙,恐江南亦将致寇了。”这语颇为太子所闻,很滋不悦。后来敬容妾弟费慧明,充导仓丞,夜盗官米,为禁司所执,交领军府惩办。敬容贻书领军将军,代为乞免。领军将军河东王萧誉,为太子纲犹子,见五十二回。当然与太子叙谈,太子即嘱令封书奏闻,梁主大怒,立将何敬容除名。敬容既去,朱异权势益专,更得引用私人,搅乱朝政。散骑常侍贺琛不忍缄默,因上书论事,略云: 窃闻慈父不爱无益之子,明君不畜无益之臣,臣荷拔擢之恩,曾不能效一职,献一言,此所以当食废飱,中宵叹息也。今特谨陈时事,具列于后,倘蒙听览,试加省鉴,如不允合,乞亮赣愚。其一事曰:今北边稽服,戈甲解息,正是生聚教训之时,而天下户口减落,关外弥甚。郡不堪州之控总,县不堪郡之裒削,更相呼扰,莫得治其政术,惟以应赴征敛为事。小民辗转流离,或依于大姓,或聚于屯封,盖不获已而窜亡,非乐之也。国 家于关外,赋税盖微,乃至年常租课,动致逋积,而民失安居,宁非牧守之过欤?东境户口空虚,皆由使命烦数,驽困邑宰,则拱手听其渔猎,桀黠长吏,又因之而为贪残,虽年降复业之诏,屡下蠲赋之恩,而民终不得反其居也。其二事曰:天下宰守,所以皆尚贪残,罕有廉白者,实由风俗侈靡使然。夫食方丈于前,所甘一味,今之燕喜,相竞夸豪,积果如山岳,列肴同绮绣,露台之产,不周一燕之资,加以歌姬盛畜,儛女盈庭,竞尚奢淫,不问品制,凡为吏牧民者,竞事剥削,虽致资巨亿,而罢归以后,不支数年。率皆尽于燕饮之物,歌讴之具。所费等于邱山,为欢止在俄顷,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,今所费之多,如复傅翼,增其搏噬,一何悖哉!其余淫侈,日见滋甚,欲使人守廉隅,吏尚清白,安可得耶!今宜严为禁制,导之以节俭,贬黜雕饰,纠奏浮华,使众皆知变其耳目,改其好恶。盖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,正雕流之弊,莫有过于俭朴者也。其三事曰: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,弘济四海以为心,不惮胼胝之劳,不辞癯瘦之苦,岂止日昃忘饥,夜分废寝。至于百司,莫不奏事,上息责下之嫌,下无逼上之咎,斯实道迈百王,事绝千载。但斗筲之人,藻棁之子,既得伏奏帷扆,便欲诡竞求进,不论国之大体,但务吹毛求疵,运挈瓶之智,侥分外之求,以深刻为能,以绳逐为务,迹虽似于奉公,事更成其威福,长弊增奸,实由于此。所愿责其公平之效,黜其邪慝之心,则上安下谧,无侥幸之患矣! 其四事曰:曩昔征伐北境,帑藏空虚,今天下无事,而犹日不暇给者,何也?去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,事省则民养,费息则财聚。止五年之中,尚能无事,必能使国丰民阜,若积以岁月,成效愈巨,斯乃范蠡灭吴之术,管仲霸齐之由。今应内省职掌,各简所部,或十省其五,成三除其一,至国容戎备,在昔应多,在今宜少,凡四方屯传邸治,或旧有,或无益,有所宜除除之,有所宜减减之,兴造有非急者,征求有可缓者,皆宜停省,以蓄财而息民,蓄其财者,正所以大用之也,息其民者,正所以大役之也。若扰其民而欲求生聚,耗其财而徒务赋敛,则奸诈盗窃,日出不已,何以语富强,图远大乎?伏思自普通以来,二十余年,刑役荐起,民力雕流,今魏氏和亲,疆埸无警,不于此时大息四民,使之殷阜,减省国费,使之储峙,一旦异境有虞,关河可扫,则国弊而民疲,事至方图,恐无及矣!臣心所谓危,罔知忌讳,谨昧死上闻! 梁主衍览书,不禁大怒,立召侍臣至前,口授教书,令他照录,大旨是诘责贺琛,令他据实指陈,不得徒托空言。第一事谓牧守贪残,应指出某官某吏,以便黜逐。第二事谓风俗侈靡,不便一一严禁,自增苛扰。朕常思本身作则,绝房室三十余年,不饮酒,不好音,雕饰各物,从未入宫。宗庙牲牢,久未宰杀,朝廷会同,只备蔬菜,且未尝奏乐。朕三更即起理事,每至日昃,日常一食,昔腰十围,今裁二尺,勤俭如许,不得谓非淳素。舍本逐末,无益于事。第三事谓百司干进,谁为诡竞?谁为吹毛求疵?谁为深刻绳逐?若不令奏事,专委一人,与秦二世宠信赵高,汉元后付托王莽,亦复何异?第四事谓省事息费,究竟何事宜省?何事宜息?国容戎备,如何减省?屯传邸治,如何裁并?何处兴造非急,何处征求可缓?宜条具以闻,不得空作漫语,徒沽直名。这道敕文,颁给贺琛,琛不禁畏缩,未敢复奏,但申表谢过罢了。原来是银样镴枪头。 大同十二年三月,梁主衍又幸同泰寺,讲三慧经,差不多过了一月,方才罢讲。再设法会,大赦天下,改元中大同。是夜同泰寺竟肇火灾,毁去浮图,梁主叹道:“这便佛经上叫作魔劫呢!”浮图成灾,并非魔劫,似你这般佞佛,却是要堕入魔劫了!遂令重造浮图十二层,格外崇闳,需工甚巨,经年未成。梁主衍年逾八十,虽精神尚可支持,终究是老态龙钟,不胜繁颐。再加平时览诵佛经,时思修寂,尤觉得耄期倦勤,厌闻政治。 是时储嗣虽定,诸子未免不平,因为梁主不立嫡孙,但立庶子,大家资格相等,没一个不觊觎神器,猜忌东宫。邵陵王纶,系梁主第六子,性最浮躁,喜怒无常,车服尝僭拟乘舆,游行无度。梁主屡戒不悛,曾将他锢置狱中,免官削爵,已而仍复旧封,命为扬州刺史,纵肆如故。遣人就市购物,不给价值,商民怨声载道,甚至罢市。府丞何智通具状上闻,纶竟遣人刺杀智通。梁主乃将纶召回,锁禁第舍,免为庶人。过了数月,又赐复封爵,何溺爱乃尔!授丹阳尹。纶恃宠生骄,妄思夺储,太子纲当然嫉视,请出纶为南徐州刺史,有诏依议。还有梁主第五予庐陵王续,出镇荆州,第七子湘东王绎,出镇江州,第八子武陵王纪,出镇益州,皆权侔人主,威福自专。惟次子豫章王综,已死北朝,四子南康王绩,长孙豫章王欢,俱已去世,免为东宫敌手。但太子纲终不自安,常挑选精卒,为自卫计。 梁主衍未察暗潮,反因舍嫡立庶的情由,未免内愧,所以待遇昭明太子诸男,不亚诸子。河东王誉得为湘州刺史,岳阳王詧,亦授雍州刺史。镴见梁主年老,朝多秕政,也不免隐蓄雄心,豫先戒备。自思襄阳形胜,为梁业开基地,正好作为根据,遂聚财下士,招募健卒数千人,环列帐下。一面究心政事,拊循士民,辖境称治。未几庐陵王续,病殁任所,调江东王绎继任。绎喜得要地,入閤欢跃,靴履为穿。 梁主怎知诸子用意,总道是孝子贤孙,不复加忧,整日里念佛诵经,蹉跎岁月。中大同二年,又复舍身同泰寺,群臣出金奉赎,如前二次故例。满望佛光普照,天子万年,哪知祸为福倚,福为祸伏,平白地得了河南,收降了一个东魏叛臣,遂闹得翻天覆地,大好江南,要变做铜驼荆棘了。直呼下文。 且说东魏大丞相高欢,自邙山战后,按兵不动,休养了两三年。东魏主善见复改元武定。嗣闻柔然与西魏连兵,将来犯境,乃亟令高欢为备。欢仍执前策,决与柔然续行修好,遣行台郎中杜弼为使,北诣柔然,申议和亲,愿为世子澄求婚。澄已有妻有妾,还要求什么婚!头兵可汗道:“高王若须自娶,愿将爱女遣嫁。”还要悖谬。杜弼归报高欢,欢年已五十,自思死多活少,不堪再偶柔然公主,因此犹豫未决。何必犹豫,将来替汝效劳,大有人在。事为娄妃所闻,遂白欢道:“为国家计,不妨从权,王无庸多疑!”欢半晌才道:“我娶番女,岂不要委屈贤妃?”娄妃道:“国事为大,家事为轻,枉尺直寻,何惜一妾!”欢一笑而罢。已而世子澄与太傅尉景,俱劝欢迎纳柔然公主,欢乃使慕容俨为纳采使,迎女南来。 欢出迎下馆,但见柔然仆从,无论男女,统皆控骑而至,就是这位新嫁娘,亦坐下一匹红鬃马,身服行装,腰佩弓矢,落落大方,毫无羞涩态度。最后随着一位番官,也是雄赳赳的少年,与新嫁娘面庞相似。欢又惊又喜,问明慕容俨,乃知送亲的随员,便是女弟秃突佳。当下彼此接见,问讯已毕,始引还晋阳城。欢妾大尔朱氏等,也出城相迎,一拥而归。柔然公主素善骑射,在途见鹍鸟飞翔,便在佩囊中取出弓矢,一发即中,鹍随箭落。大尔朱氏亦不禁技痒,由从人手中取过了弓箭,亦斜射飞鸟,应弦而落。既有此技,何不前时射死高欢,为主复仇!欢大喜道:“我得此二妇,并能击贼,岂非快事!”说着,便纵辔入城。 到了府舍,与柔然公主行结婚礼,娄妃果避出正室,令柔然公主安居。欢感激异常,寻至别室,得见娄妃,不由的五体投地,向妻拜谢。娄妃慌忙答礼,且笑且语道:“男儿膝下有千金,奈何向妾下跪!况番国公主,有所察觉,反觉不美,王尽管自去,与新人作交颈欢,不必多来顾妾了!”欢乃起身去讫。是夕老夫少妻,共效于飞,不必絮述,惟大尔朱氏器量褊窄,未及娄妃的大度,她情愿出家为尼。欢特为建筑佛寺,俾她静修。 秃突佳传述父命,谓待见外孙,然后返国,因此留居晋阳。看官!试想这高欢年经半百,精力渐衰,况他是好酒渔色,宠妾盈庭,平时已耗尽脂膏,怎能枯杨生稊,一索得男!柔然公主望儿心急,每夕嬲欢不休,累得欢形容憔悴,疾病缠身。有时入宿射堂,暂期休养,偏秃突佳硬来逼迫,定要欢去陪伴乃姊,欢稍稍推诿,秃突佳即发恶言。可怜欢无从摆脱,没奈何往就公主,力疾从事,峨眉伐性,实觉难支。欢乃想出一法,只说要出攻西魏,督军经行。肉战不如兵战。 先是西魏并州刺史王思政居守恒农,兼镇玉璧,嗣受调为荆州刺史,举韦孝宽为代。孝宽莅任后,闻高欢率军西来,即至玉璧扼守。欢至玉璧城下,昼夜围攻,孝宽随机抵御,无懈可乘。城中无水,仰给汾河,欢堵住水道,并就城南筑起土山,拟乘高扒城。城上有二楼,孝宽缚木相接,高出土山,居上临下,使不得逞。欢愤语守兵道:“虽尔缚楼至天,我自有法取尔。”因凿地为十道,穿入城中。孝宽四面掘堑,令战士屯守堑上,见有地道穿入,便塞柴投火,用皮排吹,地道变成火窟,掘地诸人,悉数焦烂。欢又改用攻车撞城,孝宽缝布为幔,悬空遮护,车不能坏。欢命兵士各执竹竿,上缚松麻,灌油加火,一面焚布,一面烧楼,孝宽用长钩钩竿,钩上有刃,得割松麻,竿仍无用。欢再穿地为二十道,中施梁柱,纵火延烧,柱折城崩。孝宽积木以待,见有崩陷,立即竖栅,欢军仍不得入。城外攻具已穷,城内守备,却还有余。 孝宽更夜出奇兵,夺据土山。 欢知不能拔,乃使参军祖珽,呼孝宽道:“君独守孤城,终难瓦全,不如早降为是!”孝宽厉声答道:“我城池严固,兵多粮足,足支数年,且孝宽是关西男子,怎肯自作降将军!”珽复语守卒道:“韦城主受彼荣禄,或当与城存亡,汝等军民,何苦随死?”守卒俱摇首不答。珽复射入赏格,谓能斩城主出降,拜太尉,封郡公,赏帛万匹。孝宽手题书背,返射城外,谓能斩高欢,准此赏格。欢苦攻至五十日,始终不能得手,士卒战死病死,约计七万人,共为一冢。大众多垂头丧气,欢亦旧病复作,入夜有大星坠欢营中,营兵大哗,乃解围引还。欢悉众攻一孤城,终不能下,所谓强弩之末,势不能穿鲁缟。当时远近讹传,谓欢已被孝宽射死。西魏又申行敕令道:“劲弩一发,凶身自殒。”欢也有所闻,勉坐厅上,引见诸贵。大司马斛律金为敕勒部人,欢使作敕勒歌,歌云: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罩四野。天苍苍,夜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斛律金为首倡,欢依声作和,语带呜咽,甚至泪下。死机已兆。自此病益沉重,好容易延过残冬,次年为武定五年,元旦日蚀,欢已不能起床,慨然叹道:“日蚀恐应在我身,我死亦无恨了!”日蚀乃天道之常,干卿甚事!遂命次子高洋,往镇邺郡,召世子澄返晋阳。 澄入问父疾,欢嘱他后事,澄独以河南为忧。欢说道:“汝非忧侯景叛乱么?”澄应声称是。欢又道:“我已早为汝算定了,景在河南十四年,飞扬跋扈,只我尚能驾驭,汝等原不能制景,我死后,且秘不发丧,库狄干、斛律金,性皆道直,终不负汝。可朱浑元、刘丰生,远来投我,当无异心。韩轨少戆,不宜苛求。彭乐轻躁,应加防护。将来能敌侯景,只有慕容绍宗一人,我未尝授彼大官,特留以待汝,汝宜厚加殊礼,委彼经略,侯景虽狡,想亦无能为了。”说至此,喉中有痰壅起,喘不成声,好一歇始觉稍平,乃复嘱澄道:“段孝先即段韶字。忠亮仁厚,智勇兼全,如有军旅大事,尽可与他商议,当不致误。”是夕遂殁,年五十二。 澄遵遗命,不发丧讣,但诡为欢书,召景诣晋阳。景右足偏短,骑射非长,独多谋算,诸将如高敖曹、彭乐等,皆为景所轻视。尝向欢陈请,愿得兵三万,横行天下,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,令作太平寺主,欢因使景统兵十万,zhuanzhi河南。景又尝藐视高澄,私语司马子如道:“高王尚在,我未敢有异心,若高王已没,却不愿与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子如忙用手掩住景口,令勿多言。景复与欢约,谓自己握兵在外,须防诈谋,此后赐书,请加微点,欢从景言,书中必加点以作暗号。高澄却未知此约,作书召景,并不加点,景遂辞不就征。且密遣人至晋阳,侦欢病状。 旋接密报,晋阳事尽归高澄主持,料知欢必不起,乃决意叛去,通书西魏,愿举河南降附。西魏授景为太傅,领河南大行台,封上谷公。景遂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,襄州刺史李密,广州刺史暴显等,潜遣兵士二百人,夜袭西兖州,被刺史邢子才探悉,一律掩获,因移檄东方诸州,各令严防。高澄即派司空韩轨,督兵讨景。 景恐关、陕一路,为轨所断,不如南向投梁,较无阻碍,乃遣郎中丁和,奉表至梁。内言臣景与高澄有隙,愿举函谷以东,瑕邱以西,如豫、广、颍、荆、襄、兖、南兖、济、东豫、洛阳、北荆、北扬等十三州内附,所有青、徐数州,但须折简,即可使服。齐、宋一平,徐事燕、赵,混一天下,便在此举云云。忽降西魏,忽附南朝,景之狡猾已可想见。梁主衍接阅景表,因召群臣廷议,尚书仆射谢举进谏道:“近来与东魏通和,边境无事,若纳彼叛臣,臣窃以为未可!”梁主怫然道:“机会难得,怎得胶柱鼓瑟?”群臣多赞成举议,请勿纳景。独有一人鼓掌道:“天与不取,反受其咎;况陛下吉梦征祥,臣曾料是混一的预兆,今言果验,奈何勿纳!”梁主亦欣然道:“诚如卿言,朕所以拟纳侯景呢。”小子有诗叹道: 竖牛入梦叔孙亡,故事曾从经传详; 尽说春秋成答问,如何迷幻自招殃!梁武曾作春秋答问,见《梁书本纪》。 究竟梁主曾梦何事,与梁主详梦,及劝纳侯景,又为何人?俟小子下回再详。 ------------- 贺琛上书言事,胪陈四则,未尝无理。梁主衍护短矜长,颁敕诘责,昏髦情形,已可概见。然读其敕文,犹令琛指实具陈,琛少振即馁,仍作寒蝉,主不明,则臣不能伸其直,于琛何尤焉!惟梁主信佛过甚,教子无方,琛上书时,亦未闻提及,舍本逐末,皮相虚谈,绳以国家大体,琛固未足知此也。高欢年已五十,尚娶蠕蠕公主,老犹渔色,不死何为?玉璧之围,五旬不下,虽由韦孝宽之善守,亦由高欢之精神不济,未能振作军心。将帅疲敝,而望士卒之振奋,不可得也。及归死晋阳,犹能智料侯景,以慕容绍宗为嘱,工心计于生前,贻智谋于身后,此其所以为乱世之雄也欤!
梁武帝信仰佛教,而太子萧纲却信奉道教,曾多次在玄圃园中讲解老庄之学。学士吴孜每次去园中听讲,尚书令何敬容便说:“昔日西晋灭亡,祸乱的根源在于崇尚虚无玄妙之学,如今东宫又重蹈覆辙,恐怕江南也将因此遭到战乱。”这话被太子听到了,很是不高兴。后来,何敬容的妾弟费慧明担任导仓丞,夜里偷盗官府粮食,被官府查办,交由领军府处理。何敬容便写信给领军将军,请求为他求情。领军将军是太子的堂侄萧誉,两人关系密切,太子便嘱咐他将信转呈给皇帝。梁武帝得知后极为愤怒,立刻将何敬容罢免职务。何敬容被罢官后,朱异的权势更加强大,还引荐私人,进一步扰乱朝政。散骑常侍贺琛心怀愤懑,于是上书直言时弊,内容大致如下:
我听说慈爱的父亲不会宠爱无用的儿子,贤明的君主不会任用无益的臣子。我承蒙提拔,却未能尽到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,更没有提出一条有用的意见,因此常常食而不饱,半夜叹息。今天我谨将当前时政的四个问题列出来,恳请陛下阅览,加以体察。如果意见不被采纳,也请明察我的苦衷。
第一件事:如今北方边境已归顺,兵器停用,正是人们安居乐业、休养生息的好时机,然而全国户口不断减少,尤其是边远地区更为严重。郡县无法承受州府的管辖,县令也无法承受郡级的过度摊派,地方之间相互掣肘,难以施展政令,只知应付征税。百姓辗转流离,有的投靠大户人家,有的聚集在军屯或封地里,都是迫不得已的逃亡,并非他们本意。国家在边远地区征收的赋税其实很少,却常常出现拖欠,百姓没有安稳的生活,这难道不是地方官员失职的表现吗?东边边境人口稀少,是由于官府派遣的使臣过多,地方官吏疲于应付,于是听任他们盘剥百姓,一些恶行贪婪的官员趁机作恶。即使朝廷反复下诏恢复农耕、减免赋税,百姓也始终无法回归故土。
第二件事:全国的地方官员大多贪污残暴,很少有廉洁清正的,这其实是社会风气奢侈浮华为因。如今人们在宴会上,吃一碗饭,只追求其中一道菜的精致,争相炫耀奢华。堆积的水果如山峰,摆放的菜肴像锦绣,甚至屋内装饰的物品,也贵重到足以买下一只野鸟。更兼蓄养歌女舞姬,厅堂盈满,争相追求奢侈放纵,不顾礼法规范。凡为官者,都以此为务,盘剥百姓。虽能积累巨额财富,但一旦退休,几年之内就因宴饮和音乐器物的开销而耗尽家产。这些花费如同堆积如山,快乐只维持片刻,事后反而怨恨自己当初所得太少,现在花费太多,若再继续这样,岂非更加贪婪暴虐?而这种奢侈之风每天都在加剧。若想让百姓守廉节、官吏清白,又怎能实现呢?应严格禁止奢侈,引导人们崇尚节俭,贬抑浮华装饰,追查浮夸行为,使大家转变自己的喜好,回归朴素本性。治理国家,必须以淳朴为根本,纠正奢侈的风气,没有比提倡节俭更重要的了。
第三件事:圣上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,心怀安定四海的抱负,不害怕辛劳,不嫌弃清贫,不只是每天忙到日落才能休息,夜里也不休息。百官争相上奏事务,上不埋怨下级,下也不逼迫上级,这确实是超越历代的治世之道。但那些品行低劣、地位卑贱的小人,一旦进入朝廷,便想通过吹毛求疵、曲解政令来谋求升迁,不顾国家大局,只图个人得利,以苛刻苛求为能,以追查小过为务。这些行为看上去看似忠于职守,实则助长了权势和贪腐,是造成腐败和弊端的根源。我恳请皇上严查这些官员的公平表现,罢黜那些邪恶自私的人心,这样上下才会安宁,国家才能免于祸患。
第四件事:过去征伐北方时,国库空虚,如今天下太平,却依然财政紧张,这是为什么?过去国家腐败混乱,就应该精简事务,节省开支,事务减少,百姓才能得到休养;开支减少,财富才能积聚。在过去五年中,尚且能维持不乱,若能继续坚持下去,国力必将强盛,百姓富足。这正是范蠡灭吴、管仲称霸的策略。现在应当整顿各部职事,精简机构,比如每十个部门裁去五个,每三个中裁去一个。至于国家军事防御,从前应多,如今应少。各地驻军、驿站、治所,若有无用的,就应裁撤;若有冗余的,就应减少。凡属非紧急的兴建工程和可以延迟的征税事项,都应暂停,以积攒财富、休养生息。只有这样,国家才能积蓄财富,才能更大规模地用于国事,让百姓得以休养,才能真正实现大用与大役。若扰民征税、耗费国财只图赋敛,必将导致盗贼滋生,怎么能谈国家富强与远大图谋呢?我回忆自普通年间以来二十多年间,刑罚和劳役不断,百姓民力已严重受损。如今魏国与我朝和亲,边境无战事,正是应趁此机会恢复百姓生计,让他们富裕起来,同时减少开支,储备财物。一旦外患来袭,边关可以迅速平定。若此时不整顿,等战事爆发时再想应对,恐怕已无及矣!我心中所忧,虽无忌讳,谨冒死上书!
梁武帝读完这封奏书,极为愤怒,立刻召见近臣,亲口命他们将这封奏章抄录,主要内容是质问贺琛,要求他实话实说,不得空谈。第一件事要指出具体官员和地方官吏,以便罢免。第二件事批评风俗奢侈,不可一一严查,以免造成过度扰民。我常以身作则,三十年不娶妻不饮酒,不喜好音乐,不追求华丽装饰,从未进入宫室。宗庙祭祀,多年未曾宰杀牲畜,朝廷会面,只备蔬菜,从不奏乐。我每天三更起身处理政事,常常到日落才休息,每天只吃一餐,过去腰围十围,现在只剩二尺。勤俭如此,怎能说我不节俭呢?他舍本逐末,毫无实际意义。
第三件事批评百官争相进言,谁在虚张声势?谁在吹毛求疵?谁在苛责他人?若不设立专人负责奏事,不将这些小事归于一人,岂不如同秦二世宠信赵高,汉元后托付王莽一样?第四件事问:到底哪些事务该精简?哪些开销该减少?军队和边境防御应如何削减?驻地驿站应如何裁撤?哪些工程非紧急可停?哪些征税可推迟?请详细列出,切莫空谈,勿图虚名。
这道敕令被下达给贺琛,贺琛吓得浑身发抖,不敢再上书,只上表谢罪。这其实是“银样镴枪头”——外表华丽,内里空虚,毫无实质。
大同十二年三月,梁武帝又到同泰寺讲《三慧经》,差不多过了一个月,才结束讲经。接着再次举行法会,大赦天下,并改元为“中大同”。当晚,同泰寺突然发生火灾,烧毁了佛塔。梁武帝感叹道:“这就是佛经里所谓的‘魔劫’!”其实这并非真正的魔劫,而是他过于迷信佛教,实则是自招灾祸,必将坠入魔障。于是下令重建佛塔,规模扩大到十二层,工程浩大,耗费巨资,多年才完成。
梁武帝年过八十,虽然精神尚可,但已显老态,体力不支,日渐疲惫。平时常诵经修道,尤其对晚年生活厌倦政事,对政治越来越反感。
这时储君虽已确定,诸子之间却互相不服,因为梁武帝不立嫡系子孙,仅立庶出子弟,诸子地位平等,人人都想争夺皇位,对太子心生猜忌。邵陵王萧纶是梁武帝第六个儿子,性情浮躁,喜怒无常,曾多次僭越皇帝仪仗,游荡无度。梁武帝屡次告诫,他也始终不改,曾一度把他关进监狱,免去官职,削去爵位,后来又恢复原职,任命为扬州刺史,依旧放纵不法。派人去市场购物,不给合理价格,百姓怨声载道,甚至罢市。府丞何智通上报朝廷,萧纶竟派人暗杀何智通。梁武帝因此将萧纶召回,关入府中,降为平民。数月后又赐其复封,宠溺有加。任命他为丹阳尹。萧纶倚仗宠爱,日渐骄横,企图夺走太子之位,太子萧纲自然嫉恨,请求将他外调为南徐州刺史,朝廷批准。其他儿子也纷纷出镇:第五子庐陵王萧续出镇荆州,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出镇江州,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出镇益州,均掌握军权,权势与皇帝相当。只有第二子豫章王萧综已死于北朝,第四子南康王萧绩,长孙豫章王萧欢,也早已去世,无从与太子相抗衡。然而太子萧纲始终不安心,常挑选精锐士兵自卫。
梁武帝未能察觉内部动荡,反而因为不立嫡子而内心愧疚,因此对诸皇子们也待遇与诸子一样。河东王萧誉被任命为湘州刺史,岳阳王萧詧也被任命为雍州刺史。面对朝政混乱,梁武帝也暗自警觉,开始蓄谋自保。他认为襄阳地势重要,是梁朝经营的根基,便聚集钱财、招揽人才,招募数千精兵,环绕帐下。同时认真思考政务,安抚百姓,境内治理称得上良好。不久庐陵王萧续在任上病亡,朝廷改由江陵王萧绎接任。萧绎得到要地,极为高兴,入宫欢跃,连鞋子都踩破了。
梁武帝根本不知诸子的野心,仍以为他们只是孝顺贤明的子孙,不加忧虑,整天诵经念佛,虚度光阴。中大同二年,他又一次舍身同泰寺,群臣出钱赎他,和前两次一样。原本希望借此得福,祈求万年长治,谁知祸从福来,福转为祸,竟然在无意识中失去了河南地区,收降了一个东魏叛将,导致局势骤变,原本繁荣的江南,顷刻间陷入战火,变成一片废墟。
再说东魏大丞相高欢,在邙山之战后,便停止进攻,休养生息两年多。东魏国主高善见改元“武定”。后听说柔然与西魏联合进犯,便急令高欢备战。高欢仍坚持先前策略,决定与柔然和亲,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北柔然,提议结盟,并请求为世子高澄迎娶柔然公主。高澄已有妻妾,又何须再娶?柔然可汗说:“高王若要娶,我愿把爱女嫁给他。”这更加荒唐。杜弼返回后报告此事,高欢便同意。后来,高欢派高澄统兵十万,前往河南。高澄曾轻视高欢,私下对司马子如说:“高王还在,我还没敢有异心;若高王死了,我不愿与这些鲜卑人共事。”司马子如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,让他不要再说。高澄还与高欢约定,自己在外掌兵,必须防范阴谋,今后写信给高欢,必须在信中加点作为暗号。而高澄并不知道这一约定,写信召高景时,未加暗号,高景遂推辞不去。同时,秘密派人前往晋阳,探查高欢的病情。
不久,得到密报:晋阳由高澄全权掌控,料定高欢必死,于是决定起兵反叛,写信投靠西魏,表示愿意归附。西魏封他为太傅,领河南大行台,封上谷公。高景于是诱捕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暴显等人,秘密派遣二百名士兵,夜间袭击西兖州,被刺史邢子才察觉,全部抓获。随即发布通告,要求各州严防。高澄立即派司空韩轨领兵讨伐。
高景害怕关中、陕西被韩轨切断,不如转而南投梁朝,阻力更小,于是派郎中丁和向梁朝递交表文。表中写道:“臣高景与高澄有矛盾,愿将函谷关以东,瑕丘以西,包括豫、广、颍、荆、襄、兖、南兖、济、东豫、洛阳、北荆、北扬等十三州归附大梁,青、徐二州则只需发一纸文书,即可归顺。若齐、宋平定,便可向燕、赵扩张,统一天下。”可见高景反复无常、狡猾奸诈。梁武帝看到高景的表文,便召集群臣商议。尚书仆射谢举进谏说:“近来我们与东魏和亲,边境安宁,若接纳这位叛臣,我私下认为不可。”梁武帝勃然大怒: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怎能死守旧法?”众臣大多赞同接纳,唯有一人拍手叫好:“天赐良机,不取反受其害;况且我曾预感陛下将有征伐大业,如今果然应验,何故拒绝?”梁武帝听了也非常高兴:“确实如此,我正是打算接纳侯景。”后人有诗叹曰:
竖牛入梦叔孙亡,故事曾从经传详;
尽说春秋成答问,如何迷幻自招殃!
梁武帝究竟梦见了什么?他与大臣详细讨论过此事,为何又决定接纳侯景?这些细节,留待下回详述。
贺琛上书言事,条理清晰,四个问题并非无理。梁武帝却护短自大,发下敕令质问,昏庸无能的统治局面已可见一斑。然而读其敕文,仍要求贺琛详细指出具体事实,结果贺琛一看到就怯懦退缩,不再直言。主上不明,臣子怎能伸张正义?对此,贺琛有何可怨呢?只是梁武帝过于迷信佛教,对子女教育无方,贺琛上书时并未提及,他所言皆浮于表面,只谈表面现象,未能触及国家根本。如果以国家大势为重,贺琛也实在不配理解。高欢年已五十,仍娶柔然公主,老来仍沉迷男女之事,不死何为?玉璧之战,五十天未能攻下,虽因韦孝宽防守得力,但主要还是高欢体弱多病,军心涣散所致。将帅疲敝,指望士卒奋勇,终是徒劳。等到最终病逝于晋阳,仍能预见侯景之乱,命人善待慕容绍宗,将计谋提前安排于身后,这是他作为乱世枭雄的智慧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