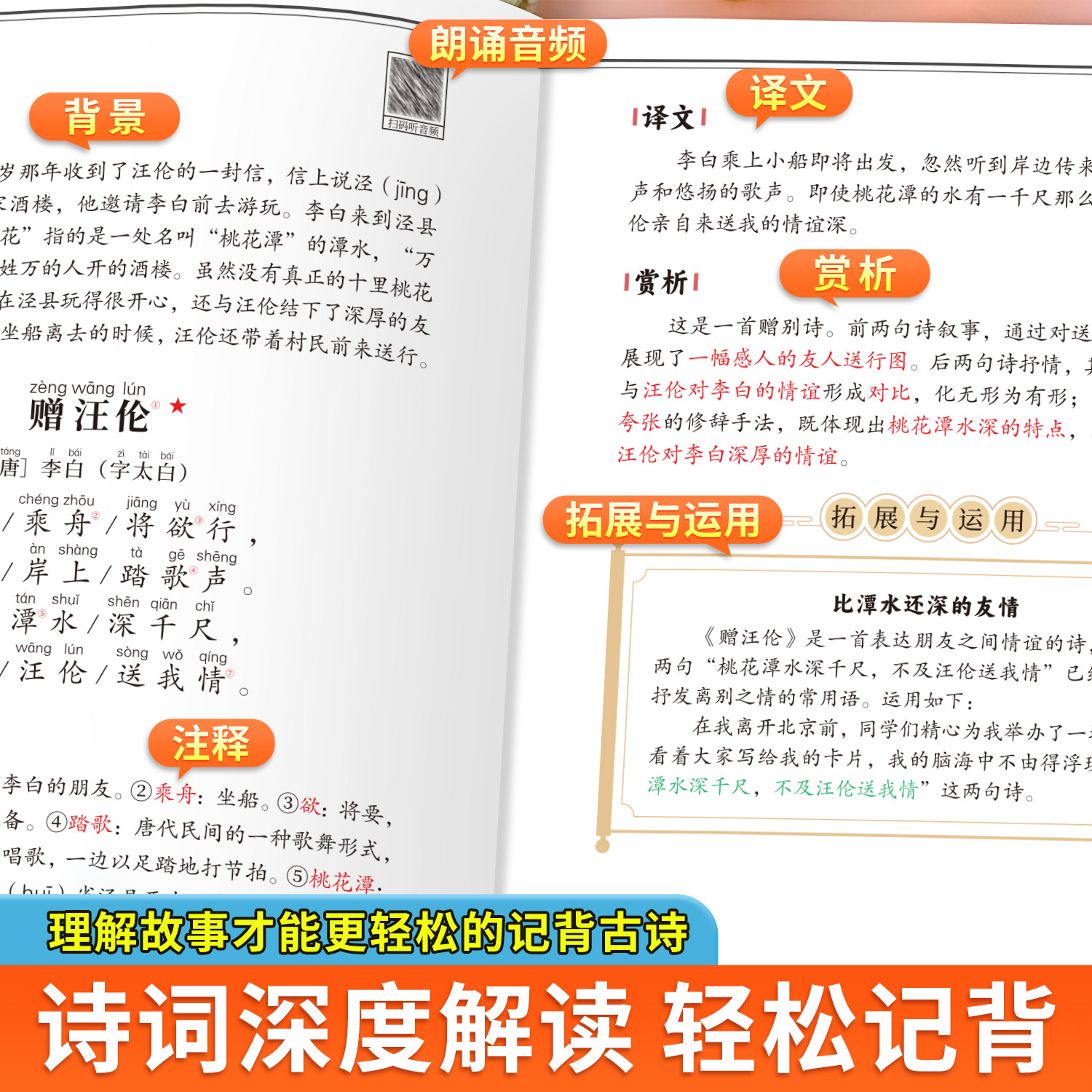卻說齊主賾永明十一年,太子長懋有疾,日加沉重,齊主賾親往東宮,臨視數次,未幾謝世,享年三十六歲,殮用袞冕,予諡文惠。長懋久在儲宮,得參政事,內外百司,都道是齊主已老,繼體在即。忽聞凶耗,無不驚惋。齊主賾抱痛喪明,更不消說。後經齊主履行東宮,見太子服玩逾度,室宇過華,不禁轉悲爲恨,飭有司隨時毀除。 太子家令沈約正奉詔編纂宋書,至欲爲袁粲立傳,未免躊躇,請旨定奪。齊主道:“袁粲自是宋室忠臣,何必多疑!”說得甚是。約又多載宋世祖孝武帝駿。太宗明帝彧。諸鄙瑣事,爲齊主所見,面諭約道:“孝武事蹟,未必盡然,朕曾經服事明帝,卿可爲朕諱惡,幸勿盡言!”約又多半刪除,不致蕪穢。 齊主因太子已逝,乃立長孫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,所有東宮舊吏,悉起爲太孫官屬。既而夏去秋來,接得魏主入寇消息。正擬調將遣兵,捍守邊境,不意龍體未適,寒熱交侵,乃徙居延昌殿,就靜養痾。乘輿方登殿階,驀聞殿屋有衰颯聲,不由的毛骨森豎,暗地驚惶。死兆已呈。但一時不便說出,只好勉入寢門,臥牀靜養。偏北寇警報,日盛一日,雍州刺史王奐,正因事伏誅,乃亟遣江州刺史陳顯達,改鎮雍州及樊城。又詔發徐陽兵丁,扼守邊要。竟陵王子良,恐兵力不足,覆在東府募兵,權命中書郎王融爲寧朔將軍,使掌召募事宜。會有敕書傳出,令子良甲仗入侍。子良應召馳入,日夕侍疾。太孫昭業,間日參承,齊主恐中外憂惶,尚力疾召樂部奏技,藉示從容。怎奈病實難支,遽致大漸,突然間暈厥過去,驚得宮廷內外,倉猝變服。獨王融年少不羈,竟欲推立子良,建定策功,便自草僞詔,意圖頒發。適太孫聞變馳至,融即戎服絳袍,出自中書省閤口,攔阻東宮衛仗,不準入內。太孫昭業,正進退兩難,忽由內侍馳出,報稱皇上覆蘇,即宣太孫入侍,融至此始不敢阻撓,只好讓他進去。其實子良卻並無妄想,與齊主談及後事,願與西昌侯蕭鸞,分掌國政。當有詔書發表道: 始終大期,賢聖不免,吾行年六十,亦復何恨;但皇業艱難,萬幾事重,不能無遺慮耳。太孫進德日茂,社稷有寄,子良善相毗輔,思弘治道,內外衆事,無論內外,可悉與鸞參決。尚書中是職務根本,悉委王晏、徐孝嗣,軍旅捍邊之略,委王敬則、陳顯達、王廣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張瓌、薛淵等,百辟庶僚,各奉爾職。謹事太孫,勿復懈怠,知復何言! 又有一道詔書,謂喪祭須從儉約,切勿浮靡,凡諸遊費,均應停止。自今遠近薦讞,務尚樸素,不得出界營求,相炫奢麗。金粟繒纊,弊民已多,珠玉玩好,傷工尤重,應嚴加禁絕,不得有違。後嗣不從,奈何!是夕齊主升遐,年五十四,在位十一年。中書郎王融,還想擁立子良,分遣子良兵仗,扼守宮禁,蕭鸞馳至雲龍門,爲甲士所阻,即厲聲叱道:“有敕召我,汝等怎得無禮?”甲士被他一叱,站立兩旁。鸞乘機衝入,至延昌殿,見太孫尚未嗣位,諸王多交頭接耳,不知何語。時長沙王晃已經病歿,高祖諸子,要算武陵王鞍爲最長,此次也在殿中。鸞趨問道:“嗣君何在?”即朗聲道:“今若立長,應該屬我,立嫡當屬太孫。”鸞應聲道:“既立太孫,應即登殿。”鞍引鸞至御寢前,正值太孫視殮,便掖令出殿,奉升御座,指麾王公,部署儀衛,片刻即定。殿中無不從命,一律拜謁,山呼萬歲。子良出居中書省,即有虎賁中郎將潘敞,奉著嗣皇面諭,率禁軍二百人,屯居太極殿西階,防備子良。子良妃袁氏,前曾撫養昭業,頗加慈愛,昭業亦樂與親近。及聞王融謀變,因與子良有隙。成服後諸王皆出,子良乞留居殿省,俟奉葬山陵,然後退歸私第,奉敕不許。王融恨所謀不遂,釋服還省,謁見子良,尚有恨聲道:“公誤我!公誤我!”子良愛融才學,嘗大度包容,所以融有唐突,子良皆置諸不理,一笑而罷。越宿傳出遺詔,授武陵王爲衛將軍,與徵南大將軍陳顯達,並開府儀同三司,西昌侯鸞爲尚書令,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,竟陵王子良爲太傅。又越數日,尊諡先帝賾爲武皇帝,廟號世祖。追尊文惠皇太子長懋爲世宗文皇帝,文惠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太后。立皇后何氏。何氏爲撫軍將軍何戢女,永明二年,納爲南郡王妃,此時從西州迎入,正位中宮。先是昭業爲南郡王時,曾從子良居西州,文惠太子常令人監製起居,禁止浪費。昭業佯作謙恭,陰實佻達,嘗夜開西州後閤,帶領僮僕,至諸營署中,召妓飲酒,備極淫樂。每至無錢可使,輒向富人乞貸,無償還期。富人不敢不與。師史仁祖,侍書胡天翼,年已衰老,由文惠太子撥令監督。兩人苦諫不從,私相語道:“今若將皇孫劣跡,上達二宮,恐不免觸怒皇孫。且足致二宮傷懷。若任他蕩佚,無以對二宮;倘有不測,不但罪及一身,並將盡室及禍。年各七十,還貪甚麼餘生呢!”遂皆仰藥自殺。二人亦可謂愚忠。昭業反喜出望外,越加縱逸,所愛左右,嘗預加官爵,書黃紙中,令他貯囊佩身,俟得登九五,依約施行。女巫楊氏,素善厭禱,昭業私下密囑,使呪詛二宮,替求天位。已而太子有疾,召令入侍,他見着太子時,似乎愁容滿面,不勝憂慮;一經出外,便與羣小爲歡。及太子病逝,臨棺哭父,擗踊號咷,彷彿一個孝子,哭罷還內,又是縱酒酣飲,歡笑如恆。世祖賾欲立太孫,嘗獨呼入內,親加撫問,每語及文惠太子,昭業不勝嗚咽,裝出一種哀慕情形。世祖還道他至性過人,呼爲法身,再三勸慰,因此決計立孫,預備繼統。至世祖有疾,又令楊氏祈他速死,且因何妃尚在西州,特暗致一書,書中不及別事,但中央寫一大喜字,外環三十六個小喜字,表明大慶的意思。有時入殿問安,見世祖病日加劇,心中非常暢快,而上卻很是憂愁。世祖與談後事,有所應諾,輒帶悽聲,世祖始終被欺,臨危尚囑咐道:“我看汝含有德性,將來必能負荷大業;但我有要囑,汝宜切記!五年以內,諸事悉委宰相,五年以後,勿復委人,若自作無成,可不至怨恨了!”哪知他不能逾期。昭業流涕聽命。至世祖彌留時候,握昭業手,且喘且語道:“汝…汝若憶翁,汝…汝當好作!”說到作字,氣逆痰衝,翻目而逝。昭業送終視殮,已不似從前失怙時,擗踊哀號。到了登殿受賀,卻是滿面喜容。禮畢返宮,竟把喪事撇置腦後,所有後宮諸妓,悉數召至,侑酒作樂,聲達戶外。此時原不必瞞人了。 過了十餘日,便密飭禁軍,收捕王融,拘繫獄中。融既下獄,乃囑使中丞孔稚珪,上書劾融,說他險躁輕狡,招納不逞,誹謗朝政,應置重刑,於是下詔賜死。融母系臨川太守謝惠宣女,夙擅文藝,嘗教融書學,因得成才。可惜融恃才傲物,常懷非望,每自嘆道:“車前無八騶,何得稱丈夫!”至是欲推戴子良,致遭主忌,因即罹禍。融上疏自訟,不得解免,更向子良求救,子良已自涉嫌疑,陰懷恐懼,哪裏還敢援手,坐令二十七歲的卓犖青年,從此畢命!少年恃才者,可援以爲戒。融臨死自嘆道:“我若不爲百歲老母,還當極言!”原來融欲指斥昭業隱惡,因恐罪及老母,所以含忍而終。 齊嗣主昭業既斬融以泄恨,遂封弟昭文爲新安王,昭秀爲臨海王,昭粲爲永嘉王。尊女巫楊氏爲楊婆,格外優待。民間爲作《楊婆兒》歌。奉祖柩出葬景安陵,未出端門,即託疾卻還,趨入後宮,傳集胡伎二部,夾閤奏樂,這真所謂縱慾敗度,癡心病狂了。 小子前敘世祖遇疾時,曾有北寇警報,至昭業嗣位,反得淫荒自盜,不聞外侮,究竟魏主曾否南侵,待小子補筆敘明。魏主宏雅懷古道,慨慕華風,興禮樂,正風俗,把從前辮髮遺制,毅然更張,也束髮爲髻,被服袞冕。且分遣牧守,祀堯舜,祭禹周公,諡孔子爲文聖尼父,告諸孔廟,另在中書省懸設孔像,親行拜祭,改中書學爲國子學,尊司徒尉元爲三老,尚書遊明根爲五更,又養國老庶老,力仿三代成制。 他尚日夕籌思,竟欲遷都洛陽,宅中居正,方足開拓宏規,因恐羣臣不從,特議大舉伐齊,乘便徙都。先在明堂右個,齋戒三日,乃命太常卿王諶筮易。可巧得了一個革卦,魏主宏喜道:“湯武革命,順天應人,這是最吉的爻筮了!”尚書任城王拓跋澄趨進道:“陛下奕葉重光,帝有中土,今欲出師南伐,反得革命爻象,恐未可謂全吉哩。”魏主宏變色道:“繇雲大人虎變,何爲不吉?”任城王澄道:“陛下龍興已久,如何今才虎變?”魏主宏厲聲道:“社稷是我的社稷,任城乃欲沮衆麼?”澄又道:“社稷原是陛下所有,臣乃是社稷臣,怎得知危不言!”魏主宏聽了此言,卻亦覺得有理,乃徐徐申說道:“各言己志,亦屬無傷。” 說畢,啓駕還宮,復召澄入議,屏人與語道:“卿以爲朕真要伐齊麼?朕思國家肇興北土,徙都平城,地勢雖固,但只便用武,不便修文,如欲移風易俗,必須遷宅中原。朕將借南征名目,就勢移居,況筮易得一革卦,正應着改革氣象,卿意以爲何如?”澄乃欣然道:“陛下欲卜宅中土,經略四海,這是周漢興隆的規制,臣亦極願贊成!”魏主宏反皺眉道:“北人習常戀故,必將驚擾,如何是好?”澄又道:“非常事業,原非常人所能曉,陛下果斷自聖衷,想彼亦無能爲了。”魏主笑道:“任城原不愧子房哩。”漢高定都關中,想是魏主記錯。遂命作河橋,指日濟師。一面傳檄遠近,調兵南征。部署至兩月有餘,乃出發平城,渡河南行,直達洛陽。 適天氣秋涼,霖雨不止,魏主宏飭諸軍前進,自著戎服上馬,執鞭指麾。尚書李衝等叩馬諫阻道:“今日南下,全國臣民,統皆不願,獨陛下毅然欲行,臣不知陛下獨往,如何成事!故敢冒死進諫。”衝果拚死,何不從馮太后於地下!魏主宏發怒道:“我方經營天下,有志混一,卿等儒生,不知大計,國家定有明刑,休得多瀆!”說着,復揚鞭欲進。安定王拓跋休等,又叩首馬前,殷勤泣諫,魏主宏說道:“此次大舉南來,震動遠近,若一無成功,如何示後?今不南伐,亦當遷都此地,庶不至師出無名。卿等如贊成遷都,可立左首,否則立右。”定安王休等均趨右側,獨南安王拓跋楨進言道:“天下事欲成大功,不能專徇衆議,陛下誠撤回南伐,遷都雒邑,這也是臣等所深願,人民的幸福呢!”說畢,即顧語羣臣,與其南伐,寧可遷都,羣臣始勉強應諾,齊呼萬歲。於是遷都議定,入城休兵。 李衝復入白道:“陛下將定鼎雒邑,宗廟宮室,非可馬上遷移,請陛下暫還平城,俟羣臣經營畢功,然後備齊法駕,蒞臨新都,方不至侷促哩。”魏主宏怫然道:“朕將巡行州郡,至鄴小停,明春方可北歸,今且緩議。”衝不敢再言。魏主即遣任城王澄馳還平城,曉諭留司百官,示明遷都利害,且餞行囑別道:“今日乃真所謂革呢。王其善爲慰諭,毋負朕命!”澄叩辭北去,魏主宏尚慮羣臣異議,更召衛尉卿徵南將軍於烈入問道:“卿意何如?”烈答道:“陛下聖略淵遠,非淺見所可測度,不過平心處議,一半樂遷,一半尚戀舊呢。”魏主宏溫顏道:“卿既不倡異議,便是贊同,朕且深感卿意。今使卿還鎮平城,一切留守庶政,可與太尉丕等悉心處置,幸勿擾民!”於烈亦拜命即行。原來魏太尉東陽王丕,與廣陵王羽,曾留守平城,未嘗隨行,故魏主復有是命。 魏主宏乃出巡東墉城,徵司空穆亮,與尚書李衝,將作大匠董爵,經營洛都。自從東墉趨河南城,順道詣滑臺,設壇告廟,頒詔大赦,再啓駕赴鄴。湊巧齊雍州刺史王奐次子王肅,奔避家難,王奐伏誅,見上文。馳至鄴城,進謁魏主,泣陳伐齊數策。魏主已經解嚴,不願南伐,惟見他語言悲惋,計議詳明,不由的契合入微,與談移晷。嗣是留侍左右,器遇日隆,或且屏人與語,到了夜半,尚娓娓不倦,幾乎相見恨晚,旋即擢肅爲輔國將軍。 適任城王澄,自平城至鄴,報稱“留司百官,初聞遷都計畫,相率驚駭,經臣援引古今,譬諭百端,已得衆心悅服,可以無虞。”魏主宏大喜道:“今非任城,朕幾不能成事了。”隨即召入王肅,諭以朕方遷都,未遑南伐,俟都城一定,當爲卿復仇。卿爲江左名士,應素習中朝掌故,所有我朝改革事宜,一以委卿,願卿勿辭!”肅唯唯遵諭,便替魏主草定禮儀,一切衣冠文物,逐條裁定,次第呈入,魏主無不嘉納,留待施行。當下在鄴西築宮,作爲行在。又命安定王休,率領官屬,往平城迎接家屬,自在行宮過了殘冬。 越年爲魏太和十八年,即齊主昭業隆昌元年,魏中書侍郎韓顯宗,上書陳事,共計四條:一是請魏主速還北都,節省遊幸諸費,移建洛京,二是請魏主營繕洛陽,應從儉約,但宜端廣衢路,通利溝渠;三是請魏主遷居洛城,應施警蹕,不宜徒率輕騎,涉履山河;四是請魏主節勞去煩,嗇神養性,惟期垂拱司契,坐保太平。魏主宏頗以爲然,乃於仲春啓行,北還平城。 留守百官迎駕入都,魏主宏登殿受朝,面諭遷都事宜。燕州刺史穆羆出奏道:“今四方未定,不應遷都,且中原無馬,如欲征伐,多形不便。”魏主宏駁道:“廄牧在代,何患無馬,不過代郡在恆山以北,九州以外,非帝王所宜都,故朕決計南遷。”尚書於栗又接入道:“臣非謂代地形勝,得過伊洛。但自先帝以來,久居此地,吏民相安,一旦南遷,未免有怫衆情。”魏主聽了,面有慍色,正要開口詰責,東陽王丕復進議道:“遷都大事,當詢諸卜筮。”魏主宏道:“昔周召聖賢,乃能卜宅。今無賢聖,問卜何益!且卜以決疑,不疑何卜!自古帝王以四海爲家,或南或北,隨地可居。朕遠祖世居北荒,平文皇帝即拓跋鬱律。始居東木根山,昭成皇帝即什翼犍。更營盛樂,道武皇帝即拓跋珪。遷都平城。朕幸叨祖蔭,國運清夷,如何獨不得遷都呢!”羣臣始不敢再言。魏主宏又復西巡,幸陰山,登閱武臺,遍歷懷朔、武川、撫冥、柔玄四鎮。及還至平城,已值秋季。到了初冬,聞洛陽宮闕,營繕粗竣,便即親告太廟,使高陽王拓跋雍,及鎮南將軍於烈,奉神主至洛陽,自率六宮后妃,及文武百官,由平城啓行,和鸞鏘鏘,旗旐央央,馳向洛都來了。小子有詩詠道: 霸圖造就慕皇風,走馬南來抵洛中; 用夏變夷懷遠略,北朝嗣主亦英雄。 魏主遷洛的時候,正值齊廷廢立的期間,欲知廢立原因,且看下回演敘。 ------------- 冡子先亡,嫡孫承重,此係古今通例,毫不足怪。蕭昭業爲文惠太子之胤,太子歿而昭業繼,祖孫相承,不背古道。議者謂昭業淫慝,難免覆亡,不若王融之推立子良,尚得保全齊高之一脈,其說是矣。然天道遠,人道邇,立孫承祖,人道也。孫無道而覆祖業,天道也。帝乙立紂,不立微子,後世不能歸咎於太史,以是相推,則於蕭鸞乎何尤!王融妄圖富貴,叛道營私,何足道哉!魏主宏南遷洛陽,本諸獨斷,後世又有譏其輕棄根本,侈襲周、漢故跡,以至再傳而微。夫國家興替,關係政治,與遷都無與,政治修明,不遷都可也;即遷都亦無不可也。否則株守故土,亦寧能不危且亡者!必謂魏主宏之遷都失策,亦屬皮相之談。本回於蕭鸞之擁立太孫,魏主宏之遷都洛邑,各無貶詞,良有以也。
齊主蕭賾在永明十一年,太子蕭長懋患病,病情日益加重,齊主親自前往東宮探望,多次慰問,不久後便去世,享年三十六歲,葬禮用的是袞冕,諡號爲“文惠”。蕭長懋長期擔任儲君,參與政事,朝廷內外都認爲齊主年老,繼承人即將上位。突然得知皇太子駕崩的消息,大家都十分震驚哀痛。齊主蕭賾悲痛欲絕,精神失常。之後齊主前往東宮巡視,發現太子的日常用品奢華,居所也過於豪華,不禁感到悲哀併產生怨恨,於是命令有關部門逐步拆除和簡化這些奢華設施。
當時,太子家令沈約正奉命編纂《宋書》,本想爲袁粲立傳,卻猶豫不決,便請求皇帝裁決。齊主說:“袁粲是宋朝忠臣,何必多疑?”這話說得很有道理。沈約還打算多記錄宋世祖孝武帝劉駿、太宗明帝劉彧的一些瑣事,但齊主看到後,立即提醒他:“孝武帝的事蹟未必真實,我曾經侍奉過明帝,你應當爲我隱瞞其中的惡事,不要說得太詳細!”沈約便刪去了許多內容,使全書不至於太過瑣碎和失實。
由於太子去世,齊主便立南郡王蕭昭業爲皇太孫,所有原屬於東宮的舊臣,都重新被任命爲太孫的屬官。不久,北方魏國進犯的消息傳來,朝廷正準備調動軍隊邊境防禦,卻不料齊主身體不適,寒熱交加,不得不退居延昌殿靜養。他剛登上殿階,忽然聽到殿內傳來房屋搖動的聲響,頓時毛骨悚然,內心驚恐。他知道自己病重將死,但一時不便說出口,只好勉強進入寢宮臥牀休養。正值北邊戰報日益緊張,雍州刺史王奐因參與謀反被處死,朝廷緊急派遣江州刺史陳顯達改任雍州及樊城的刺史。又下令徵調徐州、揚州的士兵,扼守邊境要地。竟陵王蕭子良擔心軍隊不足,便在東府招募士兵,並任命中書郎王融爲寧朔將軍,負責招募事宜。突然傳來詔書命令蕭子良佩甲帶兵入宮侍疾。蕭子良馬上遵命前往,日夜侍奉齊主。太孫蕭昭業每隔幾天也前來探視。齊主擔心內外臣民恐慌,便強撐病體,命樂部奏樂,以顯示自己從容不迫。但病情已難以支撐,突然昏倒,宮內內外都慌亂起來。只有王融年少輕狂,想趁機擁立蕭子良,建立“定策”之功,便擅自草擬假詔,想立刻發佈。恰巧太孫蕭昭業聞訊趕至,王融立刻穿着戎裝紅袍,從中書省門口衝出,攔住東宮衛兵,不讓其進入。蕭昭業進退兩難,突然有內侍飛奔出來,報告說皇帝已經轉醒,立即傳召太孫入宮侍疾。王融見狀,這纔不敢再阻攔,只好讓蕭昭業進去。其實蕭子良並無篡位之心,和齊主談完後事,表示願意與西昌侯蕭鸞共同掌管國家政事。最終朝廷發佈詔書稱:
“人終歸於死亡,賢明聖哲也無法避免。我已年過六十,還有什麼遺憾?只是國家事務繁重,治政艱難,因此難免有些憂慮。太孫德行日益增進,國家有指望。蕭子良能輔佐他,共同推行仁政,內外政務,無論是重要還是日常,都可以和蕭鸞共同商議決定。尚書省的根本事務,交由王晏、徐孝嗣處理;軍務防邊之事,交由王敬則、陳顯達、王廣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張瓌、薛淵等人負責,其他百官各盡其職。請太孫勤勉爲政,不可懈怠,還有什麼可說呢!”
又有一道詔書特別強調:喪葬祭祀必須節儉樸素,嚴禁鋪張浪費。所有不必要的開銷,一律停止。今後無論是地方還是京城,凡是舉薦官員或辦理事務,都應保持樸素,不得貪圖奢華,互相炫耀。金銀絲棉等物已嚴重損害百姓,珠玉玩好更會傷害工匠,必須嚴格禁止,不得違抗。若後世子孫不遵守,那就別怪我了!
當晚齊主去世,享年五十四歲,在位共十一年。中書郎王融仍想擁立蕭子良,甚至派人帶兵封鎖宮門,準備奪取權力。蕭鸞趕至雲龍門,遭遇甲士阻攔,便厲聲喝道:“有詔書召我,你們怎敢無禮?”甲士被他這一聲喝斥,立刻退到兩側。蕭鸞乘機衝入,到達延昌殿,見太孫尚未登基,衆王都在小聲議論,不知在說什麼。當時長沙王蕭晃已經去世,高祖諸子中,武陵王蕭鞍最長,也就在殿中。蕭鸞問:“君主是誰?”蕭鞍答道:“如果按長幼順序,應由我繼位;按嫡出原則,應由太孫登基。”蕭鸞說:“既然立了太孫,就應該馬上登殿。”蕭鞍便帶蕭鸞到御殿前,正在太孫送葬時,便暗中推動太孫走出殿外,升上寶座,下令安排王公百官,佈置儀仗,很快便定下禮制。殿中衆人無不跟隨,齊聲山呼萬歲。蕭子良被任命爲中書省長官,隨即由虎賁中郎將潘敞奉旨,率二百禁軍駐紮在太極殿西階,以防蕭子良作亂。蕭子良的夫人袁氏,早年曾撫養蕭昭業,對他非常慈愛,蕭昭業也喜歡親近她。當得知王融謀反,便與蕭子良產生了矛盾。服喪結束後,諸王陸續退下,蕭子良請求留下居於中書省,等爲先帝守陵後再退居私宅,但被皇帝明確禁止。王融因謀計失敗,脫去喪服返回中書省,見到蕭子良,仍帶着怨恨說道:“你害了我!你害了我!”蕭子良雖然欣賞王融才華,一向寬宏大量,對他的越界行爲也一笑置之,不加追究。
過了幾天,又傳出遺詔,授武陵王蕭鞍爲衛將軍,與徵南大將軍陳顯達共同開府,享有儀同三司的待遇;西昌侯蕭鸞任尚書令,太孫詹事沈文季任護軍,竟陵王蕭子良任太傅。又過幾天,追尊先帝蕭賾爲武皇帝,廟號世祖;追尊文惠太子蕭長懋爲世宗文皇帝,文惠太子妃王氏爲皇太后;立皇后何氏。何氏是撫軍將軍何戢的女兒,永明二年嫁給南郡王,此時從西州迎入宮中,正式成爲皇后。
蕭昭業在做南郡王時,曾與蕭子良一同居住在西州,文惠太子常派人監督他的起居,禁止奢侈浪費。蕭昭業表面謙恭,實際上放縱情慾,常常深夜打開西州後門,帶領僕人前往各營署,召妓飲酒,盡情享樂。每當沒錢時,便向富人借債,不講償還,富人也不好拒絕。有兩位年事已高的人物——師史仁祖和侍書胡天翼,本是文惠太子任命來監督他的。他們多次勸阻無效,私下議論道:“若把皇孫這些劣行上報給兩位君主,恐怕會惹怒皇孫,讓兩位君主傷心。如果放任不管,日後出事,不僅罪及自身,全家都可能遭受牽連。我們兩人年已七十,還貪圖什麼餘生呢!”於是都服毒自盡。他們可謂愚忠。蕭昭業得知後反而欣喜若狂,更加放縱,他寵愛的侍從,常常提前獲得官職任命,寫在黃紙上,讓其收藏佩戴,等日後登基後按約施行。女巫楊氏擅長厭勝之術,蕭昭業私下囑咐她,用法術詛咒兩位君主,幫助自己獲得皇位。後來太子生病,召楊氏入宮侍奉,他看到太子時神情憂慮,滿臉愁容,一出宮就與小人飲酒作樂。太子去世後,他親自臨棺痛哭,哀傷悲號,彷彿是一個孝子,但哭完回到宮中,又繼續縱情飲酒,如常嬉笑。
世祖蕭賾想立太孫,曾單獨召見蕭昭業,親自撫慰,每次談到文惠太子,蕭昭業都悲痛哭泣,裝出一副真摯哀傷的樣子。世祖以爲他情深性厚,稱他爲“法身”,反覆勸慰,因此決定立他爲繼承人,準備傳位給他。等到世祖病重,又讓楊氏祈求他早日死去,並特意寫了一封信給何妃(在西州),信中不談別的事,只在中央寫了“大喜”二字,周圍環繞着三十六個“大喜”字,表達大慶的喜訊。有一次進宮問安,見世祖病情日益加重,蕭昭業內心十分暢快,而世祖卻憂愁不堪。世祖與他談論後事,做出承諾時,總是帶着悽然之色。世祖始終被欺騙,臨終時還叮囑道:“我看你有德行,將來一定能成就大業。但我有重要囑託,你要牢記:五年之內,所有政事都可委任宰相,五年之後,不要再託付他人。若你自作自受,無法成就,也不至於怨恨。”蕭昭業聽後流着淚答應。世祖臨終時,握着他的手,喘着氣說:“你……你若記得我,你……你要好好做!”說到“作”字,氣逆痰湧,翻白眼,最終去世。蕭昭業送靈送葬,已不像從前失去父親那般悲痛嚎哭。等到登基受賀時,臉上卻滿是笑意。禮畢回宮,竟把喪事徹底遺忘,召集後宮所有妓女,喝酒作樂,聲音傳到門外,這已經無法掩飾。
十多日後,祕密命令禁軍逮捕王融,將其拘押入獄。王融被捕後,囑託中丞孔稚珪上書彈劾他,說他輕浮狂妄,招攬不法之徒,誹謗朝政,應受重刑,最後被下詔賜死。王融的母親是臨川太守謝惠宣的女兒,早年擅長文學,曾教他書寫讀書,因此成就了才華。可惜王融自負才華,常有不切實際的願望,常自嘆道:“車前沒有八輛馬車,怎麼能稱得上是男子漢?”如今他想推舉蕭子良,觸怒皇帝,終於遭到慘死。他上疏爲自己辯解,毫無用處,又向蕭子良求助,但蕭子良自己已有嫌疑,內心恐懼,哪裏還敢救他,最終27歲的才俊就此喪命。青年才俊若想建功立業,應以此爲戒。王融臨死前自嘆道:“如果我不是一個百歲老母,我一定會直說!”原來他想揭發蕭昭業的過失,怕牽連到年邁母親,所以只能忍住。
齊主蕭昭業殺了王融以泄憤,於是封弟弟蕭昭文爲新安王,蕭昭秀爲臨海王,蕭昭粲爲永嘉王。尊女巫楊氏爲“楊婆”,特別優待。民間甚至編出《楊婆兒》的歌曲來歌頌她。爲先帝發喪,出殯至景安陵,還沒有出端門,便託病返回後宮,傳集胡人樂伎兩部,在宮殿兩側演奏音樂,這簡直是放縱慾望、瘋狂至極了。
在世祖蕭賾患病時,曾有北邊入侵的消息。等到蕭昭業繼位後,反而沉迷享樂,不問外務,完全不知道魏國是否真的南侵。魏主拓跋宏性格懷古,嚮往中原文化,推行禮樂制度,整頓社會風氣,徹底廢除前代的辮髮舊制,改爲束髮成髻,穿着袞冕。他還派遣地方官員祭祀堯、舜、禹、周公,尊孔子爲“文聖尼父”,並親赴孔廟行祭拜儀式,在中書省設立孔子畫像,親自拜祭,將原來中書學改爲國子學,尊司徒尉元爲“三老”,尚書遊明根爲“五更”,並推廣這些制度。隨後,在鄴城建立行宮,作爲臨時都城。
第二年,即魏太和十八年(對應齊主昭業隆昌元年),魏國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,提出四條建議:第一,請求魏主儘快返回北都,節省遊歷費用,改在洛陽建都;第二,建議朝廷修繕洛陽,應節儉,但須拓寬道路,疏通溝渠;第三,遷都後,應設立警戒制度,不可輕率騎馬穿越山河;第四,應減少勞苦,安養身心,以無爲而治,守候太平。魏主拓跋宏對這四條建議非常認可,於是於仲春啓程,返回北都平城。
留守官僚迎接魏主入城,他在殿上接受朝拜,並當面說明遷都之事。燕州刺史穆羆上奏:“天下尚未安定,不應遷都,況且中原沒有良馬,若要征戰,非常不便。”魏主反駁道:“馬匹在代郡,哪裏會缺?代郡在恆山以北,屬於九域之外,非帝王應居之地,所以我決定南遷。”尚書於栗又說:“我不是說代地地形優越,能超過伊洛地區。但自先帝以來,長期居於此地,官吏百姓安居樂業,一旦南遷,恐怕會激起衆怒。”魏主聽了臉色不悅,正要發作,東陽王蕭丕進言:“遷都這種大事,應當通過占卜決定。”魏主答道:“過去周朝、召公等聖賢才能占卜選址。如今沒有賢明之士,占卜有何益處?而且占卜是爲了解疑惑,若沒有疑惑,又何必占卜?自古帝王以天下爲家,可南可北,隨地而居。我先祖世代居住北方荒野,平文帝拓跋鬱律初居東木根山,昭成帝什翼犍遷至盛樂,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。我有幸承襲祖業,國家安定,爲何就偏偏不能南遷呢?”羣臣這纔不再敢多言。
魏主又西巡至陰山,登上閱武臺,巡視懷朔、武川、撫冥、柔玄四鎮。回到平城時已正值秋季。到初冬時節,得知洛陽宮殿已基本建成,便親自前往太廟,命高陽王拓跋雍、鎮南將軍於烈奉神主前往洛陽,並率領六宮妃嬪、文武百官,從平城出發,一路上旌旗獵獵,鐘鼓齊鳴,浩浩蕩蕩奔赴洛都。
詩曰:
霸圖建立仰慕皇風,騎馬南下抵達洛陽;
推行夏制改變夷俗,北朝繼任者也稱英雄。
魏主遷都洛陽時,正值南朝齊廷廢立之亂。想了解廢立的真正原因,敬請閱讀下回內容。
——
太子先亡,嫡孫繼位,這是古今常見的制度,無可厚非。蕭昭業是文惠太子的後代,太子去世後由昭業繼承,祖孫相承,符合傳統。有人說他淫亂敗德,必然滅亡,不如王融擁立蕭子良,仍能保全齊國正統,這說法也有道理。然而,天道深遠,人道短暫。立孫承祖,是人道;孫無德而覆祖業,是天道。商紂王之父帝乙未立微子,後人不能歸咎於太史,由此推論,對蕭鸞又何須苛責!王融妄圖富貴,圖謀私利,根本不值一提。魏主拓跋宏南遷洛陽,完全是出於堅定決斷。後世有人批評他輕棄根本,盲目模仿夏周漢朝舊制,導致後代衰亡,這是一種淺薄之見。國家興衰,根本在於政治清明與否,與是否遷都無關。政治清明,不遷都也可以;政治腐敗,即使遷都也無濟於事。因此,說魏主遷都是錯誤的,不過是膚淺之論。本回對蕭鸞擁立太孫、魏主遷都洛陽均無貶低之詞,正是因爲這背後有深刻的歷史和政治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