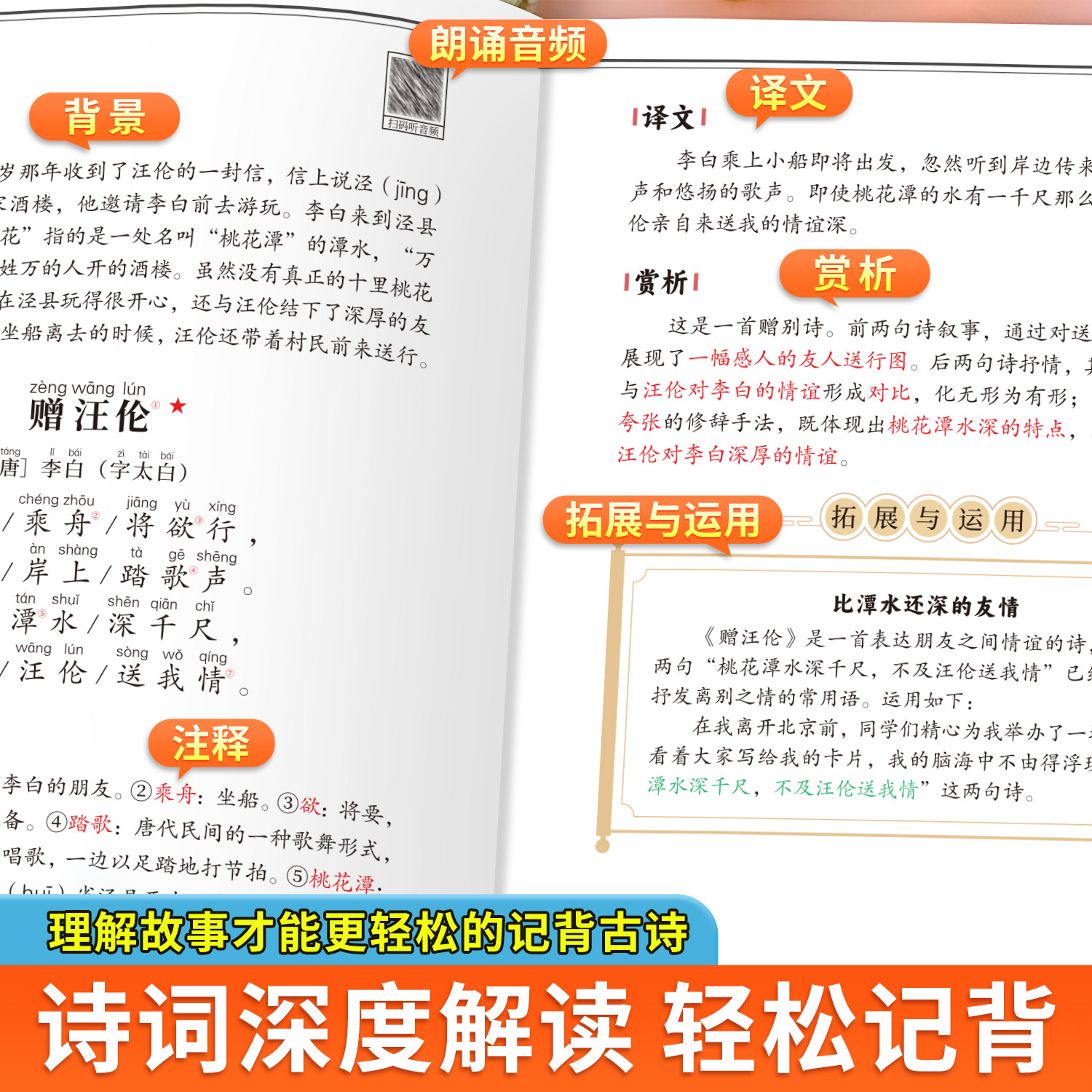《春秋左氏傳》•昭公·昭公十五年
譯文:
【經】十五年春天,周王正月,吳國國君夷末去世。二月癸酉日,在武公廟舉行祭祀儀式,樂師奏樂時,叔弓去世。樂止之後,祭祀結束。夏季,蔡國君主朝見吳國後,出逃到鄭國。六月丁巳日,發生日食。秋季,晉國荀吳率領軍隊攻打鮮虞。冬季,魯國國君前往晉國。
【傳】十五年春天,將要在武公廟舉行禘祭(祭祀祖先),朝廷下令各官員準備。梓慎說:“舉行禘祭的日子,恐怕會有災禍啊!我看到天空出現紅色和黑色的異常天象,這不是吉祥的徵兆,而是喪事的預兆,可能出在主持儀式的人身上吧?”二月癸酉日舉行禘祭,叔弓主持禮儀,樂師奏樂時,他突然去世。樂師停止演奏,儀式結束,這符合禮制。
楚國的費無極因爲妒忌朝吳在蔡國受到重用,就想讓他離開蔡國。於是他對朝吳說:“大王只信任您,才把您安置在蔡國。您年紀已經不小,卻居於下位,感到恥辱。如果一定要離開,我願意幫您向大王請求。”他又對其他貴族說:“大王只信任吳國,才把吳國安置在蔡國,你們在高位卻對他這樣,不也難嗎?如果不考慮後果,一定會遭遇禍患。”夏季,蔡國百姓果然將朝吳迎接回國內。朝吳因此逃亡至鄭國。周王大怒,說:“我只信任吳國,才把他安排在蔡國。如果沒有吳國,我根本不會有今天。你們爲什麼要拋棄他?”費無極回答說:“我哪不想留住吳國啊?只是我早先就看出他爲人與衆不同。如果讓他留在蔡國,蔡國必定會迅速叛變。所以離開吳國,正是爲了削弱蔡國的勢力。”
六月乙丑日,周王的太子壽去世。
秋季八月戊寅日,周王的穆後去世。
晉國荀吳率領軍隊討伐鮮虞,包圍鼓國。鼓國的人中有士兵建議以城池叛變,穆子(荀吳)不答應。身邊的人說:“軍隊辛苦,卻能輕易獲得城池,爲什麼不採納這個建議呢?”穆子說:“我聽叔向說過:‘對人善惡判斷不偏不倚,百姓就知道該遵循什麼,事情自然能成功。’若有人以城池來背叛我們,這是我很厭惡的事。他們若來獻城,我又能有什麼喜歡的事呢?如果獎賞那些我最厭惡的人,那還如何保證公平?如果不獎賞,又會失信於民,又怎能保護百姓?軍隊能否攻下城池,取決於實力,不強就退,不強就不進,量力而行。我絕不能因爲想得到城池而助長奸邪,這樣損失只會越來越多。”於是命鼓國人殺死叛變者,並加固防備。包圍鼓國三個月,鼓國人又有人請求投降,穆子讓鼓國人出來相見,說:“我們還有食物和力氣,暫且修整城防。”軍中將領說:“攻下城池而不佔領,白白耗費百姓的勞力和軍隊的精力,這怎麼能報答君主呢?”穆子回答說:“我是爲報效君主而戰。如果得到一座城池,卻讓百姓懈怠,那城池還有什麼意義?城池只會導致百姓懈怠,不如保住原有城池。如果百姓懈怠,軍隊也就無法作戰,喪失原有城池是不吉利的。只要鼓國人忠於其君,我同樣忠於自己的君主。只要秉持道義,善惡分明,老百姓就能知道什麼是對的,從而寧死不二心,這不是比得到城池更可貴嗎?”鼓國人報告說糧草耗盡,力氣也用盡,這才被攻下。攻下鼓國後返回,沒有俘虜一人,而是將鼓國國君鳶鞮帶回。
冬季,魯國國君前往晉國,是爲了參加平丘會盟。
十二月,晉國荀躒前往周王室,爲穆後舉行葬禮,籍談擔任隨從。葬禮結束,除去喪服,舉行宴席,用魯國的酒具敬客。周王問:“伯氏,各諸侯都配備有鎮守朝廷的官員,唯獨晉國沒有,這是什麼緣故呢?”文伯舉手讓籍談回答,籍談說:“諸侯的分封,都是從王室獲得象徵性的禮器,用來鎮守各自的國家,因此能夠向王室進獻祭祀用的禮器。晉國地處深山,與戎狄爲鄰,遠離王室,王室的影響力無法到達,甚至來不及朝拜戎狄,又怎能向王室進獻禮器呢?”周王說:“叔氏,你們難道忘記了嗎?叔父唐叔,是成王的同母弟弟,他當初得到的分封難道不是應該保留的嗎?密須國的鼓器和大路車,是成王用來舉行大祭祀的;闕鞏的鎧甲,是武王用來打敗商朝的。唐叔受賜這些器物,分封到參虛之地,用以鎮撫戎狄。後來,晉襄公得到兩輛車、金戚、鉞、秬鬯、彤弓、虎賁等禮器,從而在南陽獲得土地,鎮守東方,這不正是對有功之臣應有的酬勞嗎?凡是有功績之人,不應被遺忘,有功勞就應當被銘記,賜予土地,以器物安撫,以車服彰顯,以文章彰顯功勳,後代永遠銘記,這不就是福分嗎?如今福分得不到延續,叔父又在哪裏呢?況且你們的祖先孫伯□,曾掌管晉國的典籍,是國家的大政之臣,所以稱爲籍氏。還有辛有之子董氏,曾輔佐晉國,於是就有了董史。你們是典籍之後,爲什麼竟會忘記先祖呢?”籍談無法回答。賓客辭別後,周王說:“籍父恐怕沒有後代了!數典而忘祖。”
籍談回去後,把這件事告訴了叔向。叔向說:“周王恐怕是走不了遠了!我聽說:‘所喜愛的事必會得到終結。’現在周王既快樂又憂愁,若最終以憂愁而告終,不能說他能長久。周王一年之內就有兩年的喪事:先是太子去世,後是穆後崩逝,因此用喪禮之賓來設宴,又要求進獻禮器,這種快樂與憂愁交錯,是極不正常的,也違反禮制。禮器的進獻,是出於戰功和成就,而非出自喪事。三年之喪,即使貴爲君主也必須服喪,這是禮制。即使周王沒有真正服喪,提前舉行宴樂,這也是不合禮制的。禮是周王的根本原則。一舉一動就失掉兩項禮制,就失去了根本。如果靠背誦典籍來考據,典籍的作用是記述根本的禮儀制度,而今卻遺忘根本,只靠羅列典故,這有什麼用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