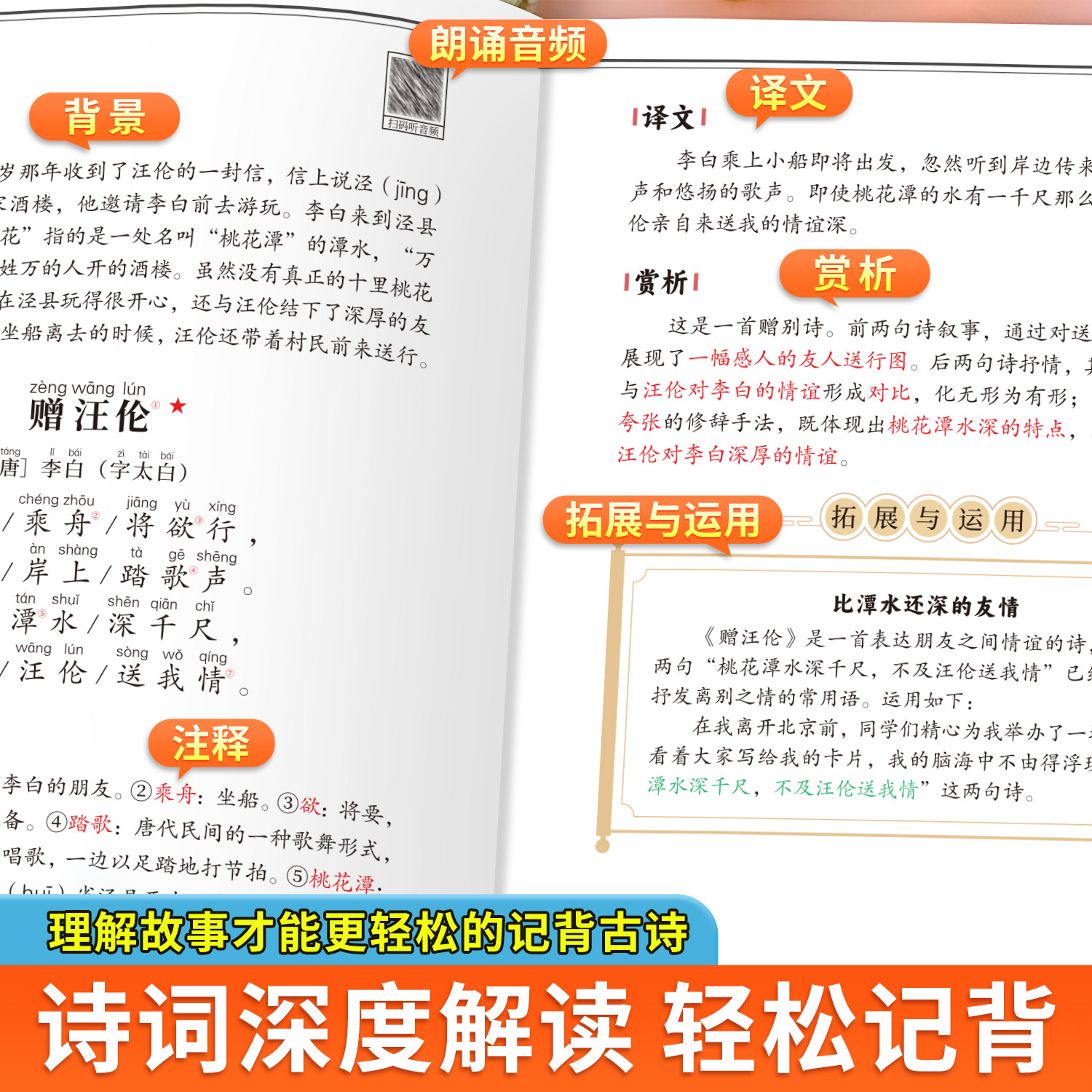《明史》•卷二百九十八·列传第一百八十六·隐逸
隐逸
韩愈言:“《蹇》之六二曰‘王臣蹇蹇’,而《蛊》之上九曰‘高尚其事’,由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。”夫圣贤以用世为心,而逸民以肥遁为节,岂性分实然,亦各行其志而已。明太祖兴礼儒士,聘文学,搜求岩穴,侧席幽人,后置不为君用之罚,然韬迹自远者,亦不乏人。迨中叶承平,声教沦浃,巍科显爵,顿天网以罗英俊,民之秀者,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。其抱瑰材,蕴积学,槁形泉石,绝意当世者,靡得而称焉。由是观之,世道升降之端,系所遭逢,岂非其时为之哉。凡征聘所及,文学行谊可称者,已散见诸传。兹取贞节超迈者数人,作《隐逸传》。
张介福 倪瓒 徐舫 杨恒 陈洄 杨引 吴海 刘闵 杨黼 孙一元沈周 陈继儒
张介福,字子祺,自怀庆徙吴中。少受学于许衡。二亲早终,遂无仕进意。家贫,冬不能具夹襦,或遗以纻絮,不受,纤介必以礼。张士诚入吴,有卒犯其家,危坐不为起。刀斫面,仆地,醒复取冠戴之,坐自若。卒怪,以为异物,走去。介福恐发其先墓,往庐焉。士诚闻而欲致之,不可。使其弟往问,答曰:“无乐乱,无贪天祸,无忘国家。”馈之,力辞。已,病革,谓其友曰:“吾志希古人,未能也。惟无污于时,庶几哉。”遂卒。
倪瓒,字元镇,无锡人也。家雄于赀,工诗,善书画。四方名士日至其门。所居有阁曰清閟,幽迥绝尘。藏书数千卷,皆手自勘定。古鼎法书,名琴奇画,陈列左右。四时卉木,萦绕其外,高木修篁,蔚然深秀,故自号云林居士。时与客觞咏其中。为人有洁癖,盥濯不离手。俗客造庐,比去,必洗涤其处。求缣素者踵至,瓒亦时应之。至正初,海内无事,忽散其赀给亲故,人咸怪之。未几兵兴,富家悉被祸,而瓒扁舟箬笠,往来震泽、三泖间,独不罹患。张士诚累欲钩致之,逃渔舟以免。其弟士信以币乞画,瓒又斥去。士信恚,他日从宾客游湖上,闻异香出葭苇间,疑为瓒也,物色渔舟中,果得之。抶几毙,终无一言。及吴平,瓒年老矣,黄冠野服,混迹编氓。洪武七年卒,年七十四。
徐舫,字方舟,桐庐人。幼轻侠,好击剑、走马、蹴踘。既而悔之,习科举业。已,复弃去,学为歌诗。睦故多诗人,唐有方干、徐凝、李频、施肩吾,宋有高师鲁、滕元秀,号睦州诗派,舫悉取步聚之。既乃游四方,交其名士,诗益工。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,舫笑曰:“吾诗人耳,可羁以章绂哉。”竟避去。筑室江皋,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,翛然若与世隔,因自号沧江散人。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章溢之赴召也,舟溯桐江,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,招基而笑,且语侵之。基望见,急延入舟中。琛、溢竞欢谑,各取冠服服之,欲载上黟川,其人不可乃止。濂初未相识,以问。基曰:“此徐方舟也。”濂因起共欢笑,酌酒而别。舫诗有《瑶林》、《沧江》二集。年六十八,丙午春,卒于家。
杨恒,字本初,诸暨人。外族方氏建义塾,馆四方游学士,恒幼往受诸经,辄领其旨要。文峻洁,有声郡邑间。浦江郑氏延为师,阅十年退居白鹿山,戴棕冠,披羊裘,带经耕烟雨间,啸歌自乐,因自号白鹿生。太祖既下浙东,命栾凤知州事。凤请为州学师,恒固让不起。凤乃命州中子弟即家问道。政有缺失,辄贻书咨访。后唐铎知绍兴,欲辟起之,复固辞。宋濂之为学士也,拟荐为国子师,闻不受州郡辟命,乃已。恒性醇笃,与人语,出肺肝相示。事稍乖名义,辄峻言指斥。家无儋石,而临财甚介,乡人奉为楷法焉。
时有陈洄者,义乌人。幼治经,长通百家言。初欲以功名显,既而隐居,戴青霞冠,披白鹿裘,不复与尘事接。所居近大溪,多修竹,自号竹溪逸民。常乘小艇,吹短箫,吹已,叩舷而歌,悠然自适。宋濂俱为之传。
杨引,吉水人。好学能诗文,为宋濂、陶安所称。驸马都尉陆贤从受学,入朝,举止端雅。太祖喜,问谁教者,贤以引对,立召见,赐食。他日,贤以亵服见,引太息曰:“是其心易我,不可久居此矣。”复以纂修征,亦不就。其教学者,先操履而后文艺。尝揭《论语乡党》篇示人曰:“吾教自有养生术,安事偃仰吐纳为。”乃节饮食,时动息,迄老视听不衰。既殁,安福刘球称其学探道原,文范后世,去就出处,卓然有陶潜、徐穉之风。
吴海,字朝宗,闽县人。元季以学行称。值四方盗起,绝意仕进。洪武初,守臣欲荐诸朝,力辞免。既而徵诣史局,复力辞。尝言:“杨、墨、释、老,圣道之贼,管、商、申、韩,治道之贼,稗官野乘,正史之贼,支词艳说,文章之贼。上之人,宜敕通经大臣,会诸儒定其品目,颁之天下,民间非此不得辄藏,坊市不得辄粥。如是数年,学者生长不涉异闻,其于养德育才,岂曰小补。”因著书一编曰《书祸》,以发明之。与永福王翰善。翰尝仕元,海数劝之死,翰果自裁。海教养其子偁,卒底成立。平居虚怀乐善,有规过者,欣然立改,因颜其斋曰闻过。为文严整典雅,一归诸理,后学咸宗仰之。有《闻过斋集》行世。
刘闵,字子贤,莆田人。生而纯悫。早孤,绝意科举,求古圣贤禔躬训家之法,率而行之。祖母及父丧未举,断酒肉,远室家。训邻邑,朔望归,则号哭殡所,如是三年。妇失爱于母,出之,独居奉养,疾不解衣。母或恚怒,则整衣竟夕跪榻前。祭享奠献,一循古礼,乡人莫不钦重。副使罗璟立社学,构养亲堂,延闵为师。提学佥事周孟中捐俸助养。知府王弼每祭庙社,必延致斋居,曰:“此人在座,私意自消。”置田二十余亩赡之,并受不辞。及母殁,即送田还官,庐墓三年。弟妇求分产,闵阖户自挝,妇感悟乃已。
弘治中,佥都御史林俊上言:“伏见皇太子年逾幼学,习处宫中,罕接外傅,豫教之道似为未备。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,然百司众职,山林隐逸,不谓无人。以臣所知,则礼部侍郎谢铎、太仆少卿储巏、光禄少卿杨廉,可备讲员。其资序未合,德行可取者二人,则致仕副使曹时中、布衣刘闵是也。闵,臣县人,恭慎醇粹,孝行高古。日无二粥,身无完衣,处之晏如。监司刘大夏、徐贯等恒敬礼之。臣谓可礼致时中为宫僚,闵以布衣入侍,必能涵育薰陶,裨益睿质。”时不能用。其后,巡按御史宗彝、饶瑭欲援诏例举闵经明行修,闵力辞。知府陈效请遂其志,荣以学职。正德元年,遥授儒学训导。
杨黼,云南太和人也。好学,读《五经》皆百遍。工篆籀,好释典。或劝其应举,笑曰:“不理性命,理外物耶?”庭前有大桂树,缚板树上,题曰桂楼。偃仰其中,歌诗自得。躬耕数亩供甘膬,但求亲悦,不顾余也。注《孝经》数万言,证群书,根性命,字皆小篆。所用砚乾,将下楼取水,砚池忽满,自是为常,时人咸异之。父母殁,为佣营葬毕,入鸡足,栖罗汉壁石窟山十余年,寿至八十。子逊迎归,一日沐浴,令子孙拜,曰:“明日吾行矣。”果卒。
孙一元,字太初,不知何许人,问其邑里,曰:“我秦人也。”尝栖太白之巅,故号太白山人。或曰安化王宗人,王坐不轨诛,故变姓名避难也。一元姿性绝人,善为诗,风仪秀朗,踪迹奇谲,乌巾白帢,携铁笛鹤瓢,遍游中原,东逾齐、鲁,南涉江、淮,历荆抵吴越,所至赋诗,谈神仙,论当世事,往往倾其座人。铅山费宏罢相,访之杭州南屏山,值其昼寝,就卧内与语。送之及门,了不酬答。宏出语人曰:“吾一生未尝见此人。”时刘麟以知府罢归,龙霓以佥事谢政,并客湖州,与郡人故御史陵昆善,而长兴吴珫隐居好客,三人者并主于其家。珫因招一元入社,称“苕溪五隐”。一元买田溪上,将老焉。举人施侃雅善一元,妻以妻妹张氏,生一女而卒,年止三十七。珫等葬之道场山。
沈周,字启南,长洲人。祖澄,永乐间举人材,不就。所居曰西庄,日置酒款宾,人拟之顾仲瑛。伯父贞吉,父恒吉,并抗隐。构有竹居,兄弟读书其中。工诗善画,臧获亦解文墨。邑人陈孟贤者,陈五经继之子也。周少从之游,得其指授。年十一,游南都,作百韵诗,上巡抚侍郎崔恭。面试《凤凰台赋》,援笔立就,恭大嗟异。及长,书无所不览。文摹左氏,诗拟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,字仿黄庭坚,并为世所爱重。尤工于画,评者谓为明世第一。
郡守欲荐周贤良,周筮《易》,得《遁》之九五,遂决意隐遁。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,图书鼎彝充牣错列,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,风流文彩,照映一时。奉亲至孝。父殁,或劝之仕,对曰:“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?奈何离膝下。”居恒厌入城市,于郭外置行窝,有事一造之。晚年,匿迹惟恐不深,先后巡抚王恕、彭礼咸礼敬之,欲留幕下,并以母老辞。
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。里人疾周者,入其姓名,遂被摄。或劝周谒贵游以免,周曰:“往役,义也,谒贵游,不更辱乎!”卒供役而还。已而守入觐,铨曹问曰:“沈先生无恙乎?”守不知所对,漫应曰:“无恙。”见内阁,李东阳曰:“沈先生有牍乎?”守益愕,复漫应曰:“有而未至。”守出,仓皇谒侍郎吴宽,问“沈先生何人?”宽备言其状。询左右,乃画壁生也。比还,谒周舍,再拜引咎,索饭,饭之而去。周以母故,终身不远游。母年九十九而终,周亦八十矣。又三年,以正德四年卒。
陈继儒,字仲醇,松江华亭人。幼颖异,能文章,同郡徐阶特器重之。长为诸生,与董其昌齐名。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。王世贞亦雅重继儒,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。继儒通明高迈,年甫二十九,取儒衣冠焚弃之。隐居昆山之阳,构庙祀二陆,草堂数椽,焚香晏坐,意豁如也。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,招之,谢弗往。亲亡,葬神山麓,遂筑室东佘山,杜门著述,有终焉之志。工诗善文,短翰小词,皆极风致,兼能绘事。又博文强识,经史诸子、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,靡不较核。或刺取琐言僻事,诠次成书,远近竞相购写。征请诗文者无虚日。性喜奖掖士类,屦常满户外,片言酬应,莫不当意去。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,吟啸忘返,足迹罕入城市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。黄道周疏称“志尚高雅,博学多通,不如继儒”,其推重如此。侍郎沈演及御史、给事中诸朝贵,先后论荐,谓继儒道高齿茂,宜如聘吴与弼故事。屡奉诏征用,皆以疾辞。卒年八十二,自为遗令,纤悉毕具。
译文:
《明史·隐逸传》翻译(现代汉语版):
韩愈曾说:“《蹇卦》六二爻说‘王室臣子勤勉不懈’,而《蛊卦》上九爻说‘高尚其志、不与尘世同流’,这是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,所追求的志节也各不相同。”圣贤之人以济世为志,而隐居高士则以退隐避世为志趣,这难道是天生如此,还是因为各自所追求的生活态度不同呢?明太祖起兵建立明朝后,大力尊崇儒士,广聘文学之士,广泛搜寻隐居山林的贤人,对隐士心怀敬重,甚至不将“不愿做官”列为罪名。然而,仍然有不少人选择隐居避世,远离尘嚣。到了中叶,天下太平,文化教育普及,科举制度兴旺,官职显赫,朝廷的网罗力量极大,天下有才之士几乎都奔赴朝廷,争名夺利。于是,那些怀抱才华、深藏学问,宁愿在山林泉石之间生活,不羡慕当世荣华的人,也就难以被世人知晓了。由此可见,社会风气的兴衰起伏,往往取决于所处的时代环境,岂非说明了时代在推动人的选择?
在这一段记载中,我们看到许多古代隐士的真实生活与精神追求:
李时中、储巏、杨廉等人,皆是德行高尚、学识渊博的隐士,可堪为皇子的老师。但明朝廷最终没有任用他们。后来巡按御史宗彝、饶瑭想依照诏令举荐隐士刘闵,刘闵坚决推辞。知府陈效希望实现他的志向,朝廷便以“学职”形式授予他荣誉。正德元年,朝廷遥授他“儒学训导”一职。
云南太和人杨黼,勤奋好学,读《五经》每部都读上百遍。他精通篆书,也喜欢研究佛经。有人劝他参加科举考试,他笑道:“人生有命,何必去追求外物?”他家门前有一棵大桂树,他用木板绑在树上,题字曰“桂楼”,在树下读书、吟诗自得其乐。他耕种几亩地,仅够维持生活,只求家庭和睦,不图多余。他写有数万字的《孝经注》,考证群书,探本溯源,笔法皆为小篆。他用的砚台十分特别,每次下去取水前,砚池都会突然满上清水,这种现象在当时人都认为是怪事。父母去世后,他为他们办完丧事,就去鸡足山,栖身于罗汉壁石窟多年,活到八十多岁。晚年回家,一日沐浴后,让子孙拜见,说:“明天我就走了。”果然去世。
孙一元,字太初,不知来自哪里,有人问他家乡,他说:“我是秦地人。”他曾在太白山顶居住,因此自号“太白山人”。有人说他是安化王的宗室,因王室谋反被诛,于是改名换姓逃离。孙一元性格卓绝,擅长写诗,风度俊朗,足迹遍布中原,东到齐、鲁,南至江、淮,经过荆楚,抵达吴越,每到一处就赋诗、谈神仙,议论世事,常常令人折服。铅山的费宏罢相后,前往杭州南屏山拜访,恰逢他午睡,就直接睡进他房间聊天。送他到门口,他竟然不回应,费宏感叹说:“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刘麟、龙霓也退休归乡,与湖州的旧友陵昆相识,而长兴人吴珫隐居好客,三人共同在吴珫家中相聚。吴珫邀请孙一元加入“苕溪五隐”团体,孙一元在溪边买地,打算晚年安居。举人施侃对他十分敬重,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,婚后生女不久便去世,年仅三十七岁。三人将他安葬在道场山。
沈周,字启南,长洲人。祖父沈澄在永乐年间考中举人,却拒绝出仕。沈家住处名为“西庄”,每日设宴款待宾客,被比作元代名士顾仲瑛。他的伯父沈贞吉和父亲沈恒吉也都崇尚隐居。家中建有竹屋,兄弟就在其中读书。沈周擅长诗文绘画,连佣人也都懂文墨。他少年时跟从陈孟贤学习,陈孟贤是陈五经之子。十岁那年,沈周到南京,写了一百韵长诗献给巡抚侍郎崔恭,并当场作《凤凰台赋》,当场成文,崔恭极为赞叹。后来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,文章模仿左丘明,诗歌仿效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,书法学黄庭坚,深受世人喜爱。尤其擅长绘画,时人评价为“明代第一”。
郡守想推荐沈周为贤良,他通过占卜《易经》,抽到“遁卦”九五爻,于是决心退隐。家中有山水亭阁,图书器物丰富,四方名士频繁来访。沈周孝顺父母,父亲去世后,有人劝他出仕,他说:“母亲把我当命根子,我怎能离开她身边呢?”他平时讨厌进入城市,只在城外租一间小屋,有事就去那里处理。晚年他刻意隐居,唯恐不彻底,被巡抚王恕、彭礼等人敬重,想留他在幕府任职,他都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。
有次县太守要征召画工为官府画屋壁,有人嫉妒沈周,就写了他的名字,将他带走。有人劝他去拜见权贵以求脱身,他回答:“我这是为公事出力,去拜贵人岂不是更让人耻辱?”最终他完成任务后返回。不久太守入朝,朝廷官员问他:“沈先生还好吗?”太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,只敷衍说:“还好。”后来在内阁见李东阳,李问他:“沈先生有没有写文章?”太守更惊讶,又答:“有,但还没送来。”出府后慌忙去见吴宽,问:“沈先生是谁?”吴宽详细说起情况。后来询问身边人,才得知此人是个画壁的“画工”。太守回到家中,去拜访沈周,再拜认错,请求吃饭,饭后离开。沈周因母亲年老,一生从未远行。母亲活到九十九岁终老,他本人也活到八十一岁。三年后,于正德四年去世。
陈继儒,字仲醇,松江华亭人。自幼聪慧,能写文章,同郡徐阶十分器重他。长大后以诸生身份闻名,与董其昌齐名。太仓王锡爵邀请他与子衡在支硎山读书。王世贞也极为敬重他,三吴地区有无数士人争相请他做老师或朋友。陈继儒志趣高远,二十多岁时,便烧毁自己的儒生衣冠,表明自己要彻底归隐。他隐居于昆山之阳,建庙祭祀两陆,仅几间草屋,每日焚香静坐,心中豁达开朗。当时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,邀请他前往,他婉拒。亲丧之后,他将父母安葬在神山脚下,便在东佘山筑室,关门著书,立志终生隐居。他工于诗文,短篇小词意境优美,又擅长书画。他博闻强识,精通经、史、诸子、术数、稗官野史甚至佛道典籍,凡细小琐事,皆能考证整理,编成书籍,远近争相购买。有人请他写诗作文,不日便有。他喜好提携后进,门前常门庭若市,回应来访者言谈举止皆得体周到。闲暇之时,他常与道士、僧人登峰临水,吟诗饮酒,忘却归途,几乎从不进城。董其昌曾为他修建“来仲楼”相邀,黄道周上疏称:“陈继儒志向高洁,学识广博,远胜于其他士人。”朝廷官员如沈演、御史、给事中等纷纷推荐,认为他德行高尚、年岁已高,应如当年举荐吴与弼一样加以礼遇。多次下诏征召,他都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。终年八十二岁,生前已写下遗嘱,事事安排详尽。
(全文整体反映了明朝中期一批读书人选择不仕、归隐山林、以修养德行、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方式,展现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疏离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