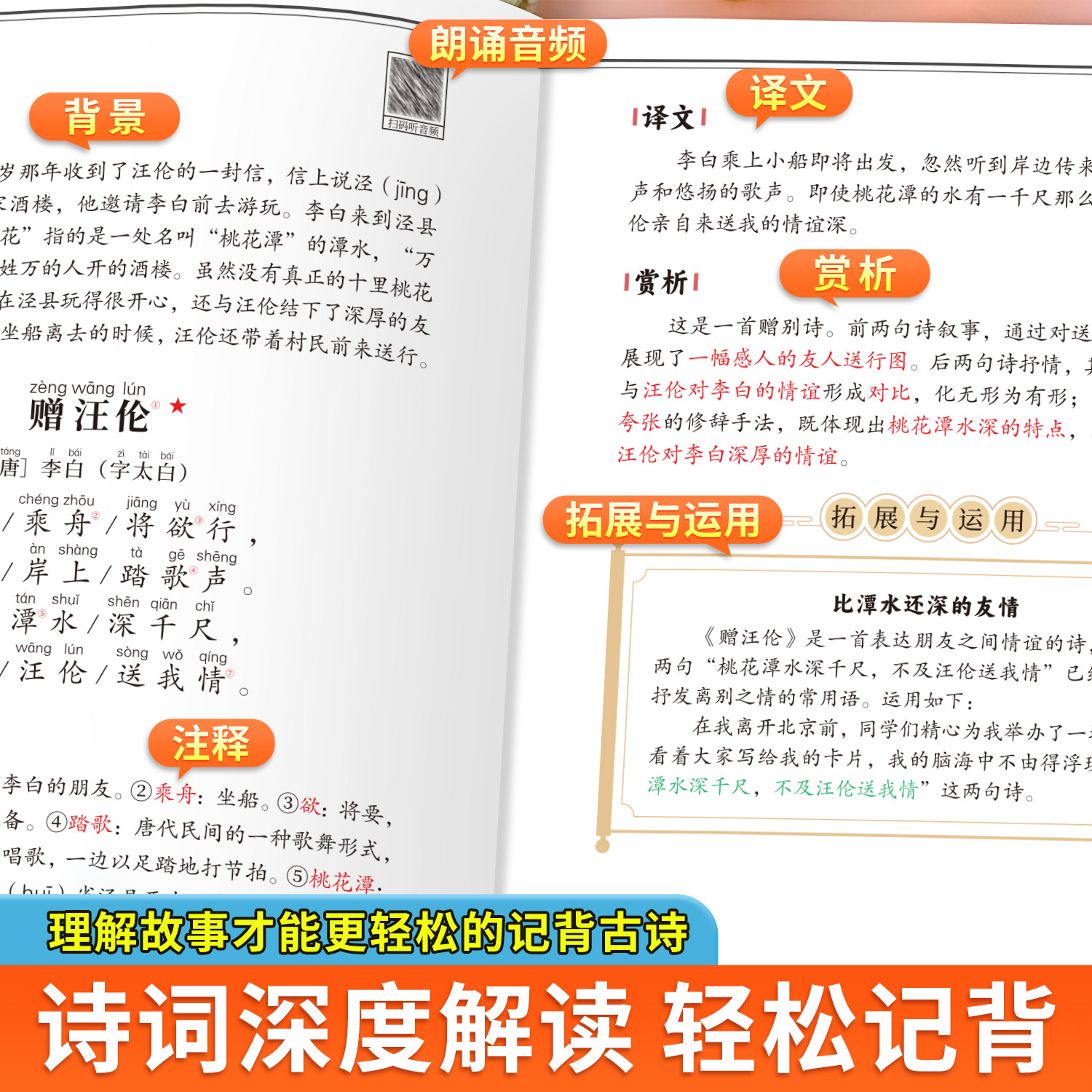儒學一
前代史傳,皆以儒學之士,分而爲二,以經藝顓門者爲儒林,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。然儒之爲學一也,《六經》者斯道之所在,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。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;而文不本於六藝,又烏足謂之文哉。由是而言,經藝文章,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。
元興百年,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,下及山林布衣之士,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,彬彬焉衆矣。今皆不復爲之分別,而採取其尤卓然成名、可以輔教傳後者,合而隸之,爲《儒學傳》。
趙復,字仁甫,德安人也。太宗乙未歲,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,德安以嘗逆戰,其民數十萬,皆俘戮無遺。進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,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、道、釋、醫、卜士,凡儒生掛俘籍者,輒脫之以歸,覆在其中。樞與之言,信奇士,以九族俱殘,不欲北,因與樞訣。樞恐其自裁,留帳中共宿。既覺,月色皓然,惟寢衣在,遽馳馬周號積屍間,無有也。行及水際,則見覆已被髮徒跣,仰天而號,欲投水而未入。樞曉以徒死無益:“汝存,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;隨吾而北,必可無他。”復強從之。先是,南北道絕,載籍不相通;至是,復以所記程、朱所著諸經傳注,盡錄以付樞。
自復至燕,學子從者百餘人。世祖在潛邸,嘗召見,問曰:“我欲取宋,卿可導之乎?”對曰:“宋,吾父母國也,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。”世祖悅,因不強之仕。惟中聞復論議,始嗜其學,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,立周子祠,以二程、張、楊、遊、朱六君子配食,選取遺書八千餘卷,請復講授其中。復以周、程而後,其書廣博,學者未能貫通,乃原羲、農、堯、舜所以繼天立極,孔子、顏、孟所以垂世立教,周、程、張、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,作《傳道圖》,而以書目條列於後;別著《伊洛發揮》,以標其宗旨。朱子門人,散在四方,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,共五十有三人,作《師友圖》,以寓私淑之志。又取伊尹、顏淵言行,作《希賢錄》,使學者知所向慕,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。樞既退隱蘇門,乃即復傳其學,由是許衡、郝經、劉因,皆得其書而尊信之。北方知有程、朱之學,自復始。
復爲人,樂易而耿介,雖居燕,不忘故土。與人交,尤篤分誼。元好問文名擅一時,其南歸也,復贈之言,以博溺心、末喪本爲戒,以自修讀《易》求文王、孔子之用心爲勉。其愛人以德類若此。復家江漢之上,以江漢自號,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。
張,字達善,其先蜀之導江人。蜀亡,僑寓江左。金華王柏,得朱熹三傳之學,嘗講道於臺之上蔡書院,從而受業焉。自《六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傳注,以及周、程、張氏之微言,朱子所嘗論定者,靡不潛心玩索,究極根柢。用功既專,久而不懈,所學益弘深微密,南北之士,鮮能及之。至元中,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,延致江寧學官,俾子弟受業,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《四書》者,皆遣從遊,或闢私塾迎之。其在維揚,來學者尤衆,遠近翕然,尊爲碩師,不敢字呼,而曰導江先生。大臣薦諸朝,特命爲孔、顏、孟三氏教授,鄒、魯之人,服誦遺訓,久而不忘。
氣宇端重,音吐洪亮,講說特精詳,子弟從之者,詵詵如也。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,夾谷之奇、楊剛中尤顯。無子。有《經說》及文集行世。吳澄序其書,以爲議論正,援據博,貫穿縱橫,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。至正中,真州守臣以及郝經、吳澄皆嘗留儀真,作祠宇祀之,曰三賢祠。
金履祥,字吉父,婺之蘭谿人。其先本劉氏,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,更爲金氏。履祥從曾祖景文,當宋建炎、紹興間,以孝行著稱,其父母疾,齋禱於天,而靈應隨至。事聞於朝,爲改所居鄉曰純孝。履祥幼而敏睿,父兄稍授之書,即能記誦。比長,益自策勵,凡天文、地形、禮樂、田乘、兵謀、陰陽、律歷之書,靡不畢究。及壯,知向濂、洛之學,事同郡王柏,從登何基之門。基則學於黃榦,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。自是講貫益密,造詣益邃。
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,履祥遂絕意進取。然負其經濟之略,亦未忍遽忘斯世也。會襄樊之師日急,宋人坐視而不敢救,履祥因進牽制搗虛之策,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、薊,則襄樊之師,將不攻而自解。且備敘海舶所經,凡州郡縣邑,下至巨洋別塢,難易遠近,歷歷可據以行。宋終莫能用。及後朱瑄、張清獻海運之利,而所由海道,視履祥先所上書,咫尺無異者,然後人服其精確。
德祐初,以迪功郎、史館編校起之,辭弗就。宋將改物,所在盜起,履祥屏居金華山中,兵燹稍息,則上下巖谷,追逐雲月,寄情嘯詠,視世故泊如也。平居獨處,終日儼然;至與物接,則盎然和懌。訓迪後學,諄切無倦,而尤篤於分義。有故人子坐事,母子分配爲隸,不相知者十年,履祥傾貲營購,卒贖以完;其子後貴,履祥終不自言,相見勞問辛苦而已。何基、王柏之喪,履祥率其同門之士,以義制服,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。
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《資治通鑑》,祕書丞劉恕爲《外紀》,以記前事,不本於經,而信百家之說,是非謬於聖人,不足以傳信。自帝堯以前,不經夫子所定,固野而難質。夫子因魯史以作《春秋》,王朝列國之事,非有玉帛之使,則魯史不得而書,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。況左氏所記,或闕或誣,凡此類皆不得以闢經爲辭。乃用邵氏《皇極經世歷》、胡氏《皇王大紀》之例,損益折衷,一以《尚書》爲主,下及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,旁採舊史諸子,表年系事,斷自唐堯以下,接於《通鑑》之前,勒爲一書,二十卷,名曰《通鑑前編》。凡所引書,輒加訓釋,以裁正其義,多儒先所未發。既成,以授門人許謙曰:“二帝三王之盛,其微言懿行,宜后王所當法,戰國申、商之術,其苛法亂政,亦后王所當戒,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。”他所著書,曰《大學章句疏義》二卷,《論語孟子集註考證》十七卷,《書表注》四卷,謙爲益加校定,皆傳於學者。天曆初,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。
初,履祥既見王柏,首問爲學之方,柏告以必先立志,且舉先儒之言:居敬以持其志,立志以定其本,志立乎事物之表,敬行乎事物之內,此爲學之大方也。及見何基,基謂之曰:“會之屢言賢者之賢,理欲之分,便當自今始。”會之,蓋柏字也。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,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,履祥則親得之二氏,而並充於己者也。
履祥居仁山之下,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。大德中卒。元統初,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,移書學官,祠履祥於鄉學。至正中,賜諡文安。
許謙,字益之,其先京兆人。九世祖延壽,宋刑部尚書。八世祖仲容,太子洗馬。仲容之子曰洸、曰洞,洞由進士起家,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。洸之子寔,事海陵胡瑗,能以師法終始者也。由平江徙婺之金華,至謙五世,爲金華人。父觥,登淳祐七年進士第,仕未顯以歿。
謙生數歲而孤,甫能言,世母陶氏口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,入耳輒不忘。稍長,肆力於學,立程以自課,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,雖疾恙不廢。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,履祥語之曰:“士之爲學,若五味之在和,醯醬既加,則酸鹹頓異。子來見我已三日,而猶夫人也,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!”謙聞之惕然。居數年,盡得其所傳之奧。於書無不讀,窮探聖微,雖殘文羨語,皆不敢忽。有不可通,則不敢強;於先儒之說,有所未安,亦不苟同也。
讀《四書章句集註》,有《叢說》二十卷,謂學者曰:“學以聖人爲準的,然必得聖人之心,而後可學聖人之事。聖賢之心,具在《四書》,而《四書》之義,備於朱子,顧其辭約意廣,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!”讀《詩集傳》,有《名物鈔》八卷,正其音釋,考其名物度數,以補先儒之未備,仍存其逸義,旁採遠援,而以己意終之。讀《書集傳》,有《叢說》六卷。其觀史,有《治忽幾微》,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,起太皞氏,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。備其世數,總其年歲,原其興亡,著其善惡。蓋以爲光卒,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,誠理亂之幾也。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,以致其意焉。
又有《自省編》,晝之所爲,夜必書之,其不可書者,則不爲也。其他若天文、地理、典章、制度、食貨、刑法、字學、音韻、醫經、術數之說,亦靡不該貫,旁而釋、老之言,亦洞究其蘊。嘗謂:“學者孰不曰闢異端,苟不深探其隱,而識其所以然,能辨其同異,別其是非也幾希。”又嘗句讀《九經》、《儀禮》及《春秋三傳》,於其宏綱要領,錯簡衍文,悉別以鉛黃朱墨,意有所明,則表而見之。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《儀禮》,視謙所定,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。謙不喜矜露,所爲詩文,非扶翼經義,張維世教,則未嘗輕筆之書也。
延祐初,謙居東陽八華山,學者翕然從之。尋開門講學,遠而幽、冀、齊、魯,近而荊、揚、吳、越,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。其教人也,至誠諄悉,內外殫盡,嘗曰:“己有知,使人亦知之,豈不快哉!”或有所問難,而詞不能自達,則爲之言其所欲言,而解其所惑。討論講貫,終日不倦,攝其粗疏,入於密微。聞者方傾耳聽受,而其出愈真切。惰者作之,銳者抑之,拘者開之,放者約之。及門之士,著錄者千餘人,隨其材分,鹹有所得。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,曰:“此義、利之所由分也。”謙篤於孝友,有絕人之行。其處世不膠於古,不流於俗。不出里閭者四十年,四方之士,以不及門爲恥,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,必即其家存問焉。或訪以典禮政事,謙觀其會通,而爲之折衷,聞者無不厭服。
大德中,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,謙以爲災在吳、楚,竊深憂之。是歲大昆,謙貌加瘠,或問曰:“豈食不足邪?”謙曰:“今公私匱竭,道殣相望,吾能獨飽邪!”其處心蓋如此。廉訪使劉庭直、副使趙宏偉,皆中州雅望,于謙深加推服,論薦於朝;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,前後章數十上;而郡復以遺逸應詔;鄉闈大比,請司其文衡。皆莫能致。至其晚節,獨以身任正學之重,遠近學者,以其身之安否,爲斯道之隆替焉。至元三年卒,年六十八。嘗以白雲山人自號,世稱爲白雲先生。朝廷賜諡文懿。
先是,何基、王柏及金履祥歿,其學猶未大顯,至謙而其道益著,故學者推原統緒,以爲朱熹之世適。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,建四賢書院,以奉祠事,而列於學官。
同郡朱震亨,字彥修,謙之高第弟子也。其清修苦節,絕類古篤行之士,所至人多化之。
陳櫟,字壽翁,徽之休寧人。櫟生三歲,祖母吳氏口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,輒成誦。五歲入小學,即涉獵經史。七歲通進士業。十五,鄉人皆師之。宋亡,科舉廢,櫟慨然發憤,致力於聖人之學,涵濡玩索,貫穿古今。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,莫若朱熹氏,熹沒未久,而諸家之說,往往亂其本真,乃著《四書發明》、《書集傳纂疏》、《禮記集義》等書,亡慮數十萬言,凡諸儒之說,有畔於朱氏者,刊而去之;其微辭隱義,則引而伸之;而其所未備者,復爲說以補其闕。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。
延祐初,詔以科舉取士,櫟不欲就試,有司強之,試鄉闈中選,遂不復赴禮部。教授於家,不出門戶者數十年。性孝友,尤剛正,日用之間,動中禮法。與人交,不以勢合,不以利遷。善誘學者,諄諄不倦。臨川吳澄,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,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,盡遣而歸櫟。櫟所居堂曰定宇,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。元統二年卒,年八十三。
揭傒斯志其墓,乃與吳澄並稱,曰:“澄居通都大邑,又數登用於朝,天下學者,四面而歸之,故其道遠而章,尊而明。櫟居萬山間,與木石俱,而足跡未嘗出鄉里,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,天下乃能知之。及其行也,亦莫之御,是可謂豪傑之士矣。”世以爲知言。
胡一桂,字庭芳,徽州婺源人。父方平。一桂生而穎悟,好讀書,尤精於《易》。初,饒州德興沈貴寶,受《易》於董夢程,夢程受朱熹之《易》黃榦,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、夢程學,嘗著《易學啓蒙通釋》。一桂之學,出於方平,得朱熹氏源委之正。宋景定甲子,一桂年十八,遂領鄉薦,試禮部不敏,退而講學,遠近師之,號雙湖先生。所著書有《周易本義附錄纂疏》、《本義啓蒙翼傳》、《朱子詩傳附錄纂疏》、《十七史纂》,並行於世。
其同郡胡炳文,字仲虎,亦以《易》名家,作《易本義通釋》,而於朱熹所著《四書》,用力尤深。餘干饒魯之學,本出於朱熹,而其爲說,多與熹牴牾,炳文深正其非,作《四書通》,凡辭異而理同者,合而一之;辭同而指異者,析而辨之,往往發其未盡之蘊。東南學者,因其所自號,稱雲峯先生。炳文嘗用薦者,署明經書院山長,再調蘭谿州學正。
黃澤,字楚望,其先長安人。唐末,舒藝知資州內江縣,卒,葬焉,子孫遂爲資州人。宋初,延節爲大理評事,兼監察御史,累贈金紫光祿大夫,澤十一世祖也。五世祖拂,與二兄播、揆,同年登進士第,蜀人榮之。父儀可,累舉不第,隨兄驥子官九江,蜀亂,不能歸,因家焉。澤生有異質,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,好爲苦思,屢以成疾,疾止復思,久之,如有所見,作《顏淵仰高鑽堅論》。蜀人治經,必先古註疏,澤於名物度數,考覈精審,而義理一宗程、朱,作《易春秋二經解》、《二禮祭祀述略》。
大德中,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,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,使食其祿以施教。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,受學者益衆。始澤嘗夢見夫子,以爲適然,既而屢夢見之,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《六經》,字畫如新,由是深有感發,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,乃作《思古吟》十章,極言聖人德容之盛,上達於文王、周公。秩滿即歸,閉門授徒以養親,不復言仕。
嘗以爲去聖久遠,經籍殘闕,傳注家率多傅會,近世儒者,又各以才識求之,故議論雖多,而經旨愈晦;必積誠研精,有所悟入,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。乃揭《六經》中疑義千有餘條,以示學者。既乃盡悟失傳之旨。自言每於幽閒寂寞、顛沛流離、疾病無聊之際得之,及其久也,則豁然無不貫通。自天地定位、人物未生已前,沿而下之,凡邃古之初,萬化之原,載籍所不能具者,皆昭若發矇,如示諸掌。然後由伏羲、神農、五帝、三王,以及春秋之末,皆若身在其間,而目擊其事者。於是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傳注之失,《詩》、《書》未決之疑,《周禮》非聖人書之謗,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,皆渙然冰釋,各就條理。故於《易》以明象爲先,以因孔子之言,上求文王、周公之意爲主,而其機括,則盡在《十翼》,作《十翼舉要》、《忘象辯》、《象略》、《辯同論》。於《春秋》以明書法爲主,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,以求向上之功,而脈絡盡在《左傳》,作《三傳義例考》、《筆削本旨》。又作《元年春王正月辯》、《諸侯娶女立子通考》、《魯隱公不書即位義》、《殷周諸侯禘祫考》、《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》,作《丘甲辯》,凡如是者十餘通,以明古今禮俗不同,見虛辭說經之無益。嘗言:“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,然後聖人本意可見,若《易象》與《春秋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,苟通其一,則可觸機而悟矣。”又懼學者得於創聞,不復致思,故所著多引而不發,乃作《易學濫觴》、《春秋指要》,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。其於禮學,則謂鄭氏深而未完,王肅明而實淺,作《禮經復古正言》。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,並崑崙、神州爲一,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,以始祖配之,而不及羣廟之社,胡宏家學不信《周禮》,以社爲祭地之類,皆引經以證其非。其辯釋諸經要旨,則有《六經補註》;詆排百家異義,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,作《翼經罪言》。近代覃思之學,推澤爲第一。
吳澄嘗觀其書,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,未有能及之者,謂人曰:“能言距楊、墨者,聖人之徒也,楚望真其人乎!”然澤雅自慎重,未嘗輕與人言。李泂使過九江,請北面稱弟子,受一經,且將經紀其家,澤謝曰:“以君之才,何經不可明,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。若餘則於艱苦之餘,乃能有見,吾非邵子,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。”泂嘆息而去。或問澤:“自閟如此,寧無不傳之懼?”澤曰:“聖經興廢,上關天運,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!”
澤家甚窶貧,且年老,不復能教授,經歲大侵,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飢,晏然曾不動其意,惟以聖人之心不明,而經學失傳,若己有罪爲大戚。至正六年卒,年八十七。其書存於世者十二三。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,得其《春秋》之學爲多。
蕭渼,字惟鬥,其先北海人。父仕秦中,遂爲奉元人。渼性至孝,自爲兒時,翹楚不凡。稍出爲府史,上官語不合,即引退,讀書面山者三十年。制一革衣,由身半以下,及臥,輒倚其榻,玩誦不少置,於是博極羣書,天文、地理、律歷、算數,靡不研究。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,惟蕭惟鬥爲識字人。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。嚐出,遇一婦人,失金釵道旁,疑渼拾之,謂曰:“殊無他人,獨翁居後耳。”渼令隨至門,取家釵以償。其婦後得所遺釵,愧謝還之。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,遇寇,欲加害,詭言“我蕭先生也”,寇驚愕釋去。
世祖分藩在秦,闢渼與楊恭懿、韓擇侍秦邸,渼以疾辭,授陝西儒學提舉,不赴。省憲大臣即其傢俱宴爲賀,使一從史先詣渼舍,渼方汲水灌園,從史至,不知其爲渼也,使飲其馬,即應之不拒,及冠帶迎賓,從史見渼,有懼色,渼殊不爲意。後累授集賢直學士、國子司業,改集賢侍讀學士,皆不赴。大德十一年,拜太子右諭德,扶病至京師,入覲東宮,書《酒誥》爲獻,以朝廷時尚酒故也。尋以病力請去職,人問其故,則曰:“在禮,東宮東面,師傅西面,此禮今可行乎?”俄除集賢學士、國子祭酒,依前右諭德,疾作,固辭而歸。卒年七十八,賜諡貞敏。
渼制行甚高,真履實踐,其教人,必自《小學》始。爲文辭,立意精深,言近而指遠,一以洙、泗爲本,濂、洛、考亭爲據,關輔之士,翕然宗之,稱爲一代醇儒。所著有《三禮說》、《小學標題駁論》、《九州志》,及《勤齋文集》,行於世。
韓擇者,字從善,亦奉元人。天資超異,信道不惑,其教學者,雖中歲以後,亦必使自《小學》等書始。或疑爲陵節勤苦,則曰:“人不知學,白首童心,且童蒙所當知,而皓首不知,可乎?”擇尤邃禮學,有質問者,口講指畫無倦容。士大夫遊宦過秦中,必往見擇,莫不虛往而實歸焉。世祖嘗召之赴京,疾,不果行。其卒也,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。
侯均者,字伯仁,亦奉元人。父母蚤亡,獨與繼母居,賣薪以給奉養。積學四十年,羣經百氏,無不淹貫,旁通釋、老外典。每讀書,必熟誦乃已。嘗言:“人讀書不至千遍,終於己無益。”故其答諸生所問,窮索極探,如取諸篋笥。名振關中,學者宗之。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,後以上疏忤時相意,不待報可,即歸休田裏。
均貌魁梧,而氣剛正,人多嚴憚之,及其應接之際,則和易款洽。雖方言古語,世所未曉者,莫不隨問而答,世鹹服其博聞。
同恕,字寬甫,其先太原人。五世祖遷秦中,遂爲奉元人。祖升。父繼先,博學能文,廉希憲宣撫陝右,闢掌庫鑰。家世業儒,同居二百口,無間言。恕安靜端凝,羈丱如成人,從鄉先生學,日記數千言。年十三,以《書經》魁鄉校。至元間,朝廷始分六部,選名士爲吏屬,關陝以恕貢禮曹,辭不行。仁宗踐阼,即其家拜國子司業,階儒林郎,使三召,不起。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,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,中書奏恕領教事,制可之。先後來學者殆千數。延祐設科,再主鄉試,人服其公。六年,以奉議大夫、太子左贊善召,入見東宮,賜酒慰問。繼而獻書,厲陳古誼,盡開悟涵養之道。明年春,英宗繼統,以疾歸。致和元年,拜集賢侍讀學士,以老疾辭。
恕之學,由程、朱上溯孔、孟,務貫浹事理,以利於行。教人曲爲開導,使得趣向之正。性整潔,平居雖大暑,不去冠帶。母張夫人卒,事異母如事所生。父喪,哀毀致目疾,時祀齋肅詳至。嘗曰:“養生有不備,事猶可復,追遠有不誠,是誣神也,可逭罪乎!”與人交,雖外無適莫,而中有繩尺。里人借騾而死,償其直,不受,曰:“物之數也,何以償爲!”家無儋石之儲,而聚書數萬卷,扁所居曰榘庵。時蕭渼居南山下,亦以道高當世,入城府,必主恕家,士論稱之曰“蕭同”。
恕自京還,家居十三年,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,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。至順二年卒,年七十八。制贈翰林直學士,封京兆郡侯,諡文貞。其所著曰《榘庵集》,二十卷。
恕弟子第五居仁,字士安,幼師蕭渼,弱冠從恕受學。博通經史,躬率子弟致力農畝,而學徒滿門。其宏度雅量,能容人所不能容。嘗行田間,遇有竊其桑者,居仁輒避之。鄉里高其行義,率多化服。作字必楷整,遊其門者,不惟學明,而行加修焉。卒之日,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,私諡之曰靜安先生。
安熙,字敬仲,真定藁城人。祖滔,父松,皆以學行淑其鄉人。熙既承其家學,及聞保定劉因之學,心向慕焉。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,因亦聞熙力於爲已之學,深許與之。熙方將造其門,而因己歿,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。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,即尊信力行之,故其教人,必尊朱氏。然因之爲人,高明堅勇,其進莫遏。熙則簡靚和易,務爲下學之功。其《告先聖文》有曰:“追憶舊聞,卒究前業。灑掃應對,謹行信言。餘力學文,窮理盡性。循循有序,發軔聖途,以存諸心,以行諸己,以及於物,以化於鄉。”其用功平實切密,可謂善學朱氏者。
熙遭時承平,不屑仕進,家居教授垂數十年,四方之來學者,多所成就。既歿,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。其門人蘇天爵,爲輯其遺文,而虞集序之曰:“使熙得見劉氏,廓之以高明,厲之以奮發,則劉氏之學,當益昌大於時矣。”
儒學一
以前的史書總是把儒學之士分爲兩類:精通經書、善於講解的稱爲“儒林”,擅長文章寫作的稱爲“文苑”。然而,儒學本爲一體,《六經》纔是儒家道統的根本所在,而文章只是用來承載和傳播這種道統的工具。因此,沒有經書的講解,文章就無法闡明其深意;而文章若不以《六經》爲基礎,又怎麼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文章呢?由此可見,經學與文章不可割裂,應當視爲一體。
元朝建立百年來,從朝廷到地方官員,從士人到平民百姓,凡是精通經學、能文達理、在當時有顯著成就的人才,數量衆多、蔚爲大觀。現在我們不按以前的分類方式加以劃分,而是選取其中德行卓著、學問深厚、能夠輔助教化、傳承道統的代表性人物,將他們合編在一起,設立《儒學傳》。
趙復,字仁甫,是湖北德安人。元太宗乙未年(公元1234年),元朝命太子闊出率兵攻打南宋,德安曾激烈抵抗,其百姓數十萬被俘殺戮殆盡。當時,楊惟中擔任中書省軍前官員,姚樞奉命在軍中徵召儒、道、釋、醫、卜等方面的才士,凡是在戰俘名單中的儒生,都讓姚樞設法釋放歸家。趙復就在其中。姚樞與他交談後,認爲他是奇才,但趙復因家族被滅,不願北上歸附,便與姚樞道別。姚樞擔心他自盡,便留他同住一帳。醒來後,只見月光明亮,牀邊只有衣衫,而趙復已不見人影。這讓他感慨萬千,更加堅定了內心信念。
後來,趙復改名換姓遠走他鄉,閉門授徒,終身不忘恢復儒學正道。他的言行舉止以儒家爲本,尤其重視心性修養與禮法實踐,成爲當時著名的經學學者。
在當時,姚樞等人非常器重趙復,認爲他深得程、朱理學精髓。他教化弟子,不唯講經,更注重修身立德,使門下多人成爲地方賢士。
另一名儒者黃澤,字楚望,是陝西人。他的先祖早年遷居四川,後世定居資州。黃澤自幼志在明經修道,善於反覆思考,常因思索過度而病倒,但病癒後仍繼續思考,久而久之,常有恍然頓悟之感,著有《顏淵仰高鑽堅論》。他特別注重經書中的名物制度,考證極爲嚴謹,且始終以程朱理學爲宗,著有《易·春秋二經解》《二禮祭祀述略》等書。
大德年間,江西行省官員聽說他的名聲,便委任他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,允許他領取俸祿以教化百姓。後來又在東湖書院設立山長職位,受學者日益增多。黃澤早年曾多次夢見孔子,起初以爲只是偶然,後來夢見孔子親授他所研讀的《六經》,字跡清晰如初,從此深感震驚,意識到自己過去所理解的經義多爲傳統敷衍之說,根本偏離了聖人本意。於是他作《思古吟》十章,深刻讚美聖人德行之盛,上達文王、周公之境。
黃澤認爲,由於距離聖人太久,經典殘缺,註疏者多隨意附會,近世儒者又各自以才智求解,導致議論雖多,反而使經義更加晦澀。唯有專心致志、誠心鑽研,才能真正把握聖人的真實之意。因此,他將《六經》中的疑難問題整理出上千條,供學者參閱。經過長期苦思,他逐步領悟了失傳已久的本義。他說,自己在孤獨寂寞、流離困苦、疾病無聊之時,常有頓悟,久而久之,所有經義都豁然貫通。
他指出,從天地未分、萬物未生之前,一直到伏羲、神農、五帝、三王,直至春秋末年,一切原初和演變的過程,以前的文獻都無法完整記錄,但他通過深思熟慮,彷彿身臨其境,親見其事。因此,他針對《易》《春秋》傳注的錯誤、《詩》《書》中尚未解決的問題、《周禮》是否爲聖人所作的爭議等,進行了深入分析,使許多長期以來無法解決的難題豁然開朗。
在《易經》方面,他強調“象”之重要,以探究孔子的本意,核心在於《十翼》,著有《十翼舉要》《忘象辯》《象略》《辯同論》等。在《春秋》方面,他強調書法的重要性,核心在於比較三傳(左傳、公羊、穀梁),以追求上達聖人之本意,著有《三傳義例考》《筆削本旨》等。他還寫了許多如《元年春王正月辯》《諸侯娶女立子通考》《魯隱公不書即位義》《殷周諸侯禘祫考》《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》《丘甲辯》等文章,闡明古代禮制與後世不同,指出空泛的言語解釋經書沒有任何益處。他認爲,若學者懂得經義被誤解的原因,就能真正看到聖人原本的意圖;而《易象》與《春秋》在解釋上的錯誤,本質相似,只要理解一種,就可觸類旁通。
他還擔心學者一旦聽說新說,便停止思考,因此在著作中常“引而不發”,以引導讀者自行探究。爲此,他著有《易學濫觴》《春秋指要》,闡明學習的根本方法。在禮學方面,他批評鄭玄註疏深奧但未盡其全,王肅註疏明瞭但淺顯,著有《禮經復古正言》,駁斥王肅將郊丘視爲一體、混同五帝、將崑崙與神州歸併等錯誤,也批評趙伯循、胡宏等人對《周禮》的誤解,皆以經典爲依據,加以論證。
吳澄讀了他的著作後說:“我一生所見的精通經義之士,還沒有人能比得上他。能駁斥楊朱、墨子之說的,是聖人的門徒,楚望,難道就是這個人嗎!”然而黃澤爲人謹慎,從不輕易與人談論學問。有人請求拜師,他婉拒說:“你有才幹,什麼經都可以明白,我不過能用筆傳授一二而已。若我講授,也是在歷經艱苦之後纔有所感悟,我並非邵雍,不敢以二十年隱居之功與你相期。”聽者歎服。
有人問他:“你長期閉門著書,是否擔心自己的學說無人傳揚?”他答:“《聖經》的興衰,關係到天運,怎能僅憑個人的努力呢?”
黃澤家境貧寒,年老後無法繼續授業,遇到大災年,家人採草根、木頭充飢,他也安然自若,只深深憂慮“聖人之心不明,經學失傳”,彷彿自己有罪一般,非常痛心。至正六年(1346年)去世,享年八十七歲。他遺留的著作僅存十二三份,其中門人新安趙汸繼承併發揚了他《春秋》學說,最爲精通。
蕭渼,字惟鬥,先祖爲北海人,父親在秦地任職,遂成爲奉元(今陝西西安)人。他極爲孝順,自幼出類拔萃,後來離開官府任職,隱居山中讀書達三十年。他製備一種特殊衣袍,從腰以下到躺臥時都倚靠在牀榻邊,專心誦讀,因此博通羣書,天文、地理、曆法、算數無所不精。侯均曾感嘆:“元朝建立百年,真正識字讀書、通曉經義的人,只有蕭惟鬥一人。”
蕭渼門下學生衆多,有人外出遇到一位婦人遺失金釵,懷疑是蕭渼所拾,便說:“除了你,別人都沒看見,只有你居後。”蕭渼命她到家中,取出家中的釵鈿還她。那婦人後來找到了自己遺失的釵,十分感激,還之。有個從城中歸來的人,途中遭遇強盜,強盜謊稱自己是“蕭先生”,嚇得逃走。
世祖分封在陝西時,徵召蕭渼與楊恭懿、韓擇侍奉秦王,蕭渼以身體有病爲由推辭,後被任命爲陝西儒學提舉,他未赴任。省裏的官員到他家設宴慶賀,派一名下屬先去探望,卻不知是蕭渼,下屬見他汲水澆園,便讓其餵馬,蕭渼未拒絕。等到對方穿戴整齊來拜訪,見到他時,下人神情驚懼,蕭渼卻不以爲意。後來多次提拔爲集賢直學士、國子司業、集賢侍讀學士等,他皆不赴任。大德十一年,被任命爲太子右諭德,以病體堅持前往京城,入宮向太子獻《酒誥》一文,是因當時朝廷崇尚酒風,希望通過此文勸誡。不久因病請求辭官,有人問原因,他回答:“按照古禮,太子東面而坐時,師傅應西面而立,如今這種禮制是否還能實行?”不久又被任命爲集賢學士、國子祭酒,仍以右諭德身份兼任,但因病復發,堅決辭歸。去世時年七十八,追諡“貞敏”。
蕭渼品行高潔,言行一致,教育學生時必從《小學》(即基礎道德修養)入手。他所作文章寓意深遠,語言精煉卻立意高遠,始終以孔子、顏回爲根本,以程朱理學爲依據。關中地區的人們都尊稱他爲一代醇儒,其著作如《三禮說》《小學標題駁論》《九州志》《勤齋文集》等廣爲流傳。
韓擇,字從善,同樣來自奉元。天賦異稟,篤信儒道,教育學生時,即使年歲已長,也堅持從《小學》等基礎典籍開始。有人懷疑他過於嚴格,他回答:“若人不懂學習,到了晚年纔開始學,豈不是白首如童子?而童蒙階段本應瞭解的基本道理,難道到了晚年才能知道嗎?”韓擇尤其精通禮學,有學生向他提問,他總是一口講出、手指畫圖,從不倦怠。士大夫遊宦途經陝西,必前往拜訪,無不受益而歸。世祖曾召他入京,但他病重未能成行。他去世時,門人服喪達百人之多。
侯均,字伯仁,也來自奉元。父母早亡,獨自與繼母生活,靠賣柴維持生計。他四十年如一日地讀書,精通諸經百家,旁通佛老典籍。他讀書必背誦千遍才放心,曾說:“人若讀書不到千遍,終究無益。”因此,每當學生提問,他都能窮究極探,如同從箱中取出珍寶。他的名聲震動關中,成爲衆多學子的師表。後被推薦爲太常博士,因上書觸怒權臣,不久便辭職歸鄉。
侯均身材魁梧,性格剛正,人多敬畏,但與人交往時卻和藹可親。即便對方提出古語、生僻詞句,他都能應答自如,天下人皆稱讚他博聞強識。
同恕,字寬甫,祖籍太原,五代祖遷居秦中,遂成爲奉元人。祖父升,父親繼先,學識淵博,擅長文章,曾任廉希憲宣撫使的幕僚,掌管倉庫鑰匙。家族世代爲儒,兄弟姐妹數百人同居,毫無嫌隙。同恕性格沉靜莊重,少年時便像成人一般,跟鄉間先生學習,每日記誦數千言。十三歲便以《尚書》在鄉試中拔得頭籌。
元朝初年,朝廷正式設立六部,選拔名士爲官,關中陝西以同恕的學識入貢禮部,他辭而不應。仁宗即位後,特地前往他家中,任命爲國子司業,官至儒林郎,朝廷三度徵召,他皆不赴任。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奏請在奉元設立“魯齋書院”,由朝廷批准,同恕擔任山長,後來曾兩次主持鄉試,被世人敬服。至元六年,被召爲太子左贊善,入宮面見太子,賜酒慰問,隨後上書力陳古禮與修養之道,深受太子賞識。第二年,英宗即位,因病歸鄉。至和元年,再被任命爲集賢侍讀學士,以年老多病推辭。
同恕的學問,從程朱理學溯源至孔子、孟子,致力於貫通事理,用於實際生活。他教學生時總是耐心誘導,使他們明白方向。他性情嚴謹,即使在酷暑,也從不脫去衣冠。母親張夫人去世,他以對待親生之母的態度侍奉外母。父親去世,他悲痛欲絕,導致眼病,祭祀時肅穆嚴謹。他曾說:“養生不完,尚可補救;但追思祖先不誠,就是欺騙神靈,豈能免除罪責!”與人交往,看似不親近,實則有原則、有底線。有鄉人借馬被殺,他主動賠償,卻不收錢,說:“這是物之常數,何須賠償?”家中財產極其匱乏,卻收藏書籍數萬卷,自號“榘庵”(意爲“有度量的居所”)。當時蕭渼也以德行著稱,入城府時必定去同恕家中拜訪,鄉人稱“蕭同”,以表敬重。
同恕從京城返回後,長期居家,朝廷官員視他如稀世之才,鄉里人稱他“先生”,不再用姓氏稱呼。至順二年去世,享年七十八歲,朝廷追贈翰林直學士,封京兆郡侯,諡號“文貞”。其著作爲《榘庵集》,共二十卷。
同恕的弟子第五居仁,字士安,年少時師從蕭渼,二十歲左右隨同恕學習,精通經史,帶領子弟從事農耕,門下弟子衆多。他胸懷寬廣,氣度不凡,能容人之不能容。曾有一次在田間行走,發現有人偷了他的桑樹,他立刻避開,不與爭執。鄉里人對他行義深感佩服,紛紛效仿。他寫字工整,門下弟子不僅學問精進,而且品行也更加端正。去世時,門人商議爲其追加諡號,私諡“靜安先生”。
安熙,字敬仲,是真定藁城人。祖上父母皆以學問德行感化鄉里。安熙繼承家學,後來聽聞保定劉因的學問,十分嚮往。安熙家與劉因相隔數百里,劉因已去世,便通過劉因的弟子烏叔備瞭解其學術思想。劉因自得朱熹著作後,便深信併力行,因此他教人時,必定尊崇朱熹。然而劉因爲人高明堅定,志向不可阻擋;而安熙則性格簡樸溫和,注重從基礎做起,主張踏實練習。他《告先聖文》中寫道:“回憶往昔所學,終歸於自身修養;打掃房間、應對長幼,謹言慎行;勤學苦讀,力求明理知性;循序漸進,踏上聖人之路,用以存心,用以實踐,推及世間,化育鄉里。”他用功踏實、細緻入微,是真正善於學習朱熹學說的人。
安熙處世平和,不慕功名,居家講學達數十年,四方來學者皆受益。他去世後,鄉人於藁城西筦鎮爲他立祠。他的門人蘇天爵收集了他遺留的著作,虞集爲此作序,說:“如果安熙能見到劉因,受其高明之風的啓發,再加以奮發之力,那麼劉因的學說,一定能在當時更廣泛傳播、大放異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