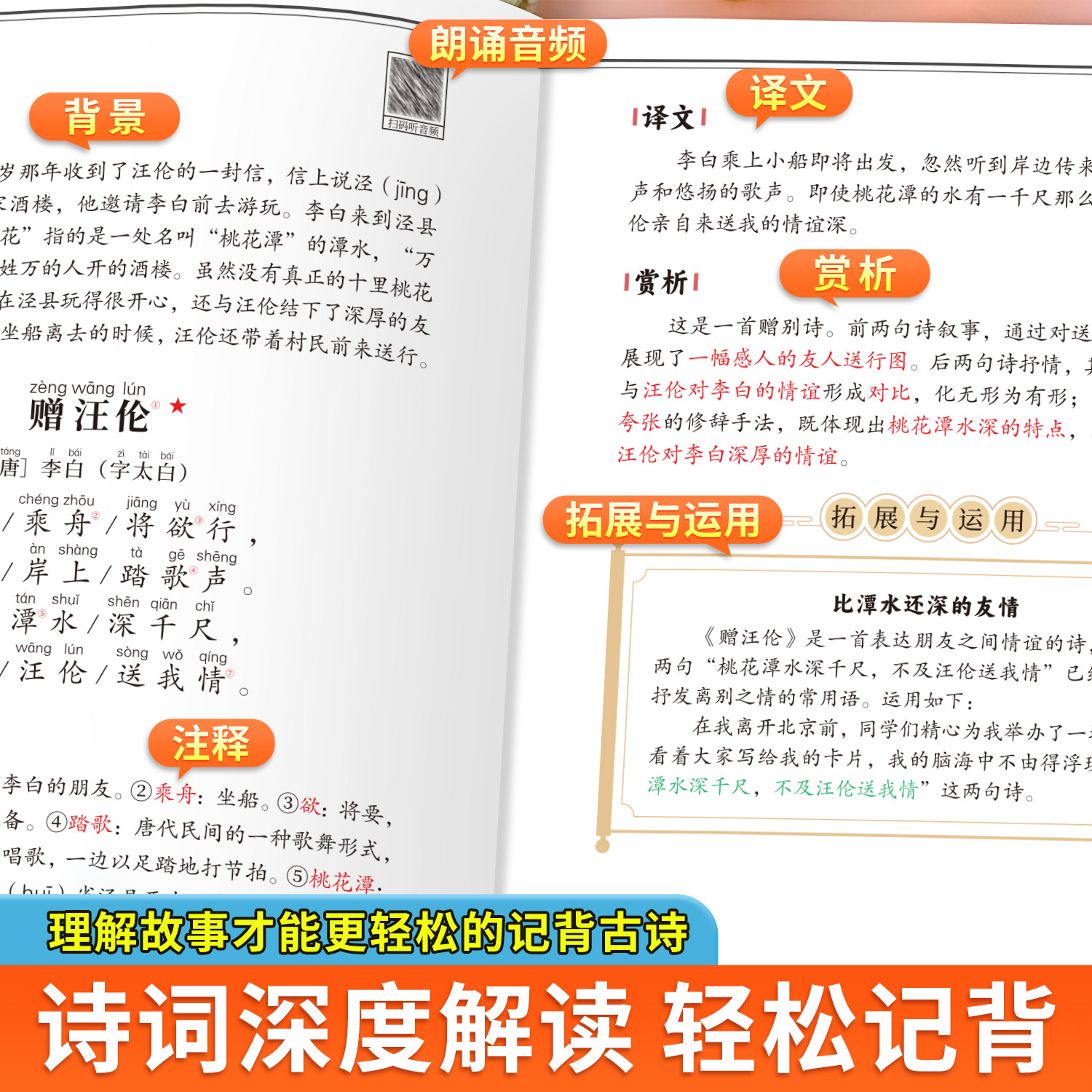太史公曰:餘每讀虞書,至於君臣相敕,維是幾安,而股肱不良,萬事墮壞,未嘗不流涕也。成王作頌,推己懲艾,悲彼家難,可不謂戰戰恐懼,善守善終哉?君子不爲約則修德,滿則棄禮,佚能思初,安能惟始,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,非大德誰能如斯!傳曰“治定功成,禮樂乃興”。海內人道益深,其德益至,所樂者益異。滿而不損則溢,盈而不持則傾。凡作樂者,所以節樂。君子以謙退爲禮,以損減爲樂,樂其如此也。以爲州異國殊,情習不同,故博採風俗,協比聲律,以補短移化,助流政教。天子躬於明堂臨觀,而萬民鹹盪滌邪穢,斟酌飽滿,以飾厥性。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,嘄噭之聲興而士奮,鄭衛之曲動而心淫。及其調和諧合,鳥獸盡感,而況懷五常,含好惡,自然之勢也?
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,封君世闢,名顯鄰州,爭以相高。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,雖退正樂以誘世,作五章以剌時,猶莫之化。陵遲以至六國,流沔沈佚,遂往不返,卒於喪身滅宗,並國於秦。
秦二世尤以爲娛。丞相李斯進諫曰:“放棄詩書,極意聲色,祖伊所以懼也;輕積細過,恣心長夜,紂所以亡也。”趙高曰:“五帝、三王樂各殊名,示不相襲。上自朝廷,下至人民,得以接歡喜,合殷勤,非此和說不通,解澤不流,亦各一世之化,度時之樂,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?”二世然之。
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,令小兒歌之。高祖崩,令沛得以四時歌鳷宗廟。孝惠、孝文、孝景無所增更,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。
至今上即位,作十九章,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,拜爲協律都尉。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,皆集會五經家,相與共講習讀之,乃能通知其意,多爾雅之文。
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,以昏時夜祠,到明而終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。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。春歌青陽,夏歌硃明,秋歌西昚,冬歌玄冥。世多有,故不論。
又嘗得神馬渥窪水中,複次以爲太一之歌。曲曰:“太一貢兮天馬下,霑赤汗兮沫流赭。騁容與兮跇萬里,今安匹兮龍爲友。”後伐大宛得千里馬,馬名蒲梢,次作以爲歌。歌詩曰:“天馬來兮從西極,經萬里兮歸有德。承靈威兮降外國,涉流沙兮四夷服。”中尉汲黯進曰:“凡王者作樂,上以承祖宗,下以化兆民。今陛下得馬,詩以爲歌,協於宗廟,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?”上默然不說。丞相公孫弘曰:“黯誹謗聖制,當族。”
凡音之起,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動,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,故形於聲;聲相應,故生變;變成方,謂之音;比音而樂之,及干鏚羽旄,謂之樂也。樂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,其聲噍以殺;其樂心感者,其聲嘽以緩;其喜心感者,其聲發以散;其怒心感者,其聲粗以厲;其敬心感者,其聲直以廉;其愛心感者,其聲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,感於物而後動,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。故禮以導其志,樂以和其聲,政以壹其行,刑以防其奸。禮樂刑政,其極一也,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動於中,故形於聲,聲成文謂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,其正和;亂世之音怨以怒,其正乖;亡國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聲音之道,與正通矣。宮爲君,商爲臣,角爲民,徵爲事,羽爲物。五者不亂,則無怗懘之音矣。宮亂則荒,其君驕;商亂則搥,其臣壞;角亂則憂,其民怨;徵亂則哀,其事勤;羽亂則危,其財匱。五者皆亂,迭相陵,謂之慢。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。鄭衛之音,亂世之音也,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,亡國之音也,其政散,其民流,誣上行私而不可止。
凡音者,生於人心者也;樂者,通於倫理者也。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,禽獸是也;知音而不知樂者,衆庶是也。唯君子爲能知樂。是故審聲以知音,審音以知樂,審樂以知政,而治道備矣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,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。禮樂皆得,謂之有德。德者得也。是故樂之隆,非極音也;食饗之禮,非極味也。清廟之瑟,硃弦而疏越,一倡而三嘆,有遺音者矣。大饗之禮,尚玄酒而俎腥魚,大羹不和,有遺味者矣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,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,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。
人生而靜,天之性也;感於物而動,性之頌也。物至知知,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,知誘於外,不能反己,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,而人之好惡無節,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,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,有淫佚作亂之事。是故彊者脅弱,衆者暴寡,知者詐愚,勇者苦怯,疾病不養,老幼孤寡不得其所,此大亂之道也。是故先王制禮樂,人爲之節:衰麻哭泣,所以節喪紀也;鐘鼓干鏚,所以和安樂也;婚姻冠笄,所以別男女也;射鄉食饗,所以正交接也。禮節民心,樂和民聲,政以行之,刑以防之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,則王道備矣。
樂者爲同,禮者爲異。同則相親,異則相敬。樂勝則流,禮勝則離。合情飾貌者,禮樂之事也。禮義立,則貴賤等矣;樂文同,則上下和矣;好惡著,則賢不肖別矣;刑禁暴,爵舉賢,則政均矣。仁以愛之,義以正之,如此則民治行矣。
樂由中出,禮自外作。樂由中出,故靜;禮自外作,故文。大樂必易,大禮必簡。樂至則無怨,禮至則不爭。揖讓而治天下者,禮樂之謂也。暴民不作,諸侯賓服,兵革不試,五刑不用,百姓無患,天子不怒,如此則樂達矣。合父子之親,明長幼之序,以敬四海之內。天子如此,則禮行矣。
大樂與天地同和,大禮與天地同節。和,故百物不失;節,故祀天祭地。明則有禮樂,幽則有鬼神,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。禮者,殊事合敬者也;樂者,異文合愛者也。禮樂之情同,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與時並,名與功偕。故鐘鼓管磬羽籥干鏚,樂之器也;詘信俯仰級兆舒疾,樂之文也。簠簋俎豆制度文章,禮之器也;升降上下週旋裼襲,禮之文也。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,識禮樂之文者能術。作者之謂聖,術者之謂明。明聖者,術作之謂也。
樂者,天地之和也;禮者,天地之序也。和,故百物皆化;序,故羣物皆別。樂由天作,禮以地制。過制則亂,過作則暴。明於天地,然後能興禮樂也。論倫無患,樂之情也;欣喜驩愛,樂之也。中正無邪,禮之質也;莊敬恭順,禮之制也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,越於聲音,用於宗廟社稷,事于山川鬼神,則此所以與民同也。
王者功成作樂,治定製禮。其功大者其樂備,其治辨者其禮具。干鏚之舞,非備樂也;亨孰而祀,非達禮也。五帝殊時,不相沿樂;三王異世,不相襲禮。樂極則憂,禮粗則偏矣。及夫敦樂而無憂,禮備而不偏者,其唯大聖乎?天高地下,萬物散殊,而禮制行也;流而不息,合同而化,而樂興也。春作夏長,仁也;秋斂冬藏,義也。仁近於樂,義近於禮。樂者敦和,率神而從天;禮者辨宜,居鬼而從地。故聖人作樂以應天,作禮以配地。禮樂明備,天地官矣。
天尊地卑,君臣定矣。高卑已陳,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,小大殊矣。方以類聚,物以羣分,則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。地氣上隮,天氣下降,陰陽相摩,天地相蕩,鼓之以雷霆,奮之以風雨,動之以四時,暖之以日月,而百化興焉,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。
化不時則不生,男女無別則亂登,此天地之情也。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,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,窮高極遠而測深厚,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。著不息者天也,著不動者地也。一動一靜者,天地之間也。故聖人曰“禮雲樂雲”。
昔者舜作五絃之琴,以歌南風;夔始作樂,以賞諸侯。故天子之爲樂也,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,五穀時孰,然後賞之以樂。故其治民勞者,其舞行級遠;其治民佚者,其舞行級短。故觀其舞而知其德,聞其諡而知其行。大章,章之也;咸池,備也;韶,繼也;夏,大也;殷周之樂盡也
天地之道,寒暑不時則疾,風雨不節則飢。教者,民之寒暑也,教不時則傷世。事者,民之風雨也,事不節則無功。然則先王之爲樂也,以法治也,善則行象德矣。夫豢豕爲酒,非以爲禍也;而獄訟益煩,則酒之流生禍也。是故先王因爲酒禮,一獻之禮,賓主百拜,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,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。故酒食者,所以合歡也。
樂者,所以象德也;禮者,所以閉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,必有禮以哀之;有大福,必有禮以樂之:哀樂之分,皆以禮終。
樂也者,施也;禮也者,報也。樂,樂其所自生;而禮,反其所自始。樂章德,禮報情反始也。所謂大路者,天子之輿也;龍旂九旒,天子之旌也;青黑緣者,天子之葆龜也;從之以牛羊之羣,則所以贈諸侯也。
樂也者,情之不可變者也;禮也者,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,禮別異,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。窮本知變,樂之情也;著誠去僞,禮之經也。禮樂順天地之誠,達神明之德,降興上下之神,而凝是精粗之體,領父子君臣之節。
是故大人舉禮樂,則天地將爲昭焉。天地欣合,陰陽相得,煦嫗覆育萬物,然後草木茂,區萌達,羽翮奮,角生,蟄蟲昭穌,羽者嫗伏,毛者孕鬻,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,則樂之道歸焉耳。
樂者,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幹揚也,樂之末節也,故童者舞之;布筵席,陳樽俎,列籩豆,以升降爲禮者,禮之末節也,故有司掌之。樂師辯乎聲詩,故北面而弦;宗祝辯乎宗廟之禮,故後屍;商祝辯乎喪禮,故後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,成而下;行成而先,事成而後。是故先王有上有下,有先有後,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。
樂者,聖人之所樂也,而可以善民心。其感人深,其風移俗易,故先王著其教焉。
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,而無哀樂喜怒之常,應感起物而動,然後心術形焉。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,而民思憂;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,而民康樂;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,而民剛毅;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,而民肅敬;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,而民慈愛;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,而民淫亂。
是故先王本之情性,稽之度數,制之禮義,合生氣之和,道五常之行,使之陽而不散,陰而不密,剛氣不怒,柔氣不懾,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,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。然後立之學等,廣其節奏,省其文采,以繩德厚也。類小大之稱,比終始之序,以象事行,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:故曰“樂觀其深矣”。
土敝則草木不長,水煩則魚鱉不大,氣衰則生物不育,世亂則禮廢而樂淫。是故其聲哀而不莊,樂而不安,慢易以犯節,流湎以忘本。廣則容奸。狹則思欲,感滌盪之氣而滅平和之德,是以君子賤之也。
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,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,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倡和有應,回邪曲直各歸其分,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。
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,比類以成其行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,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,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,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,以行其義。然後發以聲音,文以琴瑟,動以干鏚,飾以羽旄,從以簫管,奮至德之光,動四氣之和,以著萬物之理。是故清明象天,廣大象地,終始象四時,周旋象風雨;五色成文而不亂,八風從律而不奸,百度得數而有常;小大相成,終始相生,倡和清濁,代相爲經。故樂行而倫清,耳目聰明,血氣和平,移風易俗,天下皆寧。故曰“樂者樂也”。君子樂得其道,小人樂得其欲。以道制欲,則樂而不亂;以欲忘道,則惑而不樂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,廣樂以成其教,樂行而民鄉方,可以觀德矣。
德者,性之端也;樂者,德之華也;金石絲竹,樂之器也。詩,言其志也;歌,詠其聲也;舞,動其容也:三者本乎心,然後樂氣從之。是故情深而文明,氣盛而化神,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,唯樂不可以爲僞。
樂者,心之動也;聲者,樂之象也;文采節奏,聲之飾也。君子動其本,樂其象,然後治其飾。是故先鼓以警戒,三步以見方,再始以著往,復亂以飭歸,奮疾而不拔,極幽而不隱。獨樂其志,不厭其道;備舉其道,不私其欲。是以情見而義立,樂終而德尊;君子以好善,小人以息過:故曰“生民之道,樂爲大焉”。
君子曰: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。致樂以治心,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。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,樂則安,安則久,久則天,天則神。天則不言而信,神則不怒而威。致樂,以治心者也;致禮,以治躬者也。治躬則莊敬,莊敬則嚴威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,而鄙詐之心入之矣;外貌斯須不莊不敬,而慢易之心入之矣。故樂也者,動於內者也;禮也者,動於外者也。樂極和,禮極順。內和而外順,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,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,理髮乎外而民莫不承順,故曰“知禮樂之道,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”。
樂也者,動於內者也;禮也者,動於外者也。故禮主其謙,樂主其盈。禮謙而進,以進爲文;樂盈而反,以反爲文。禮謙而不進,則銷;樂盈而不反,則放。故禮有報而樂有反。禮得其報則樂,樂得其反則安。禮之報,樂之反,其義一也。
夫樂者樂也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諸聲音,形於動靜,人道也。聲音動靜,性術之變,盡於此矣。故人不能無樂,樂不能無形。形而不爲道,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,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,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,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,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,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,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,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是故樂在宗廟之中,君臣上下同聽之,則莫不和敬;在族長鄉里之中,長幼同聽之,則莫不和順;在閨門之內,父子兄弟同聽之,則莫不和親。故樂者,審一以定和,比物以飾節,節奏合以成文,所以合和父子君臣,附親萬民也,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故聽其雅頌之聲,志意得廣焉;執其干鏚,習其俯仰詘信,容貌得莊焉;行其綴兆,要其節奏,行列得正焉,進退得齊焉。故樂者天地之齊,中和之紀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
夫樂者,先王之所以飾喜也;軍旅鈇鉞者,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。喜則天下和之,怒則暴亂者畏之。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。
魏文侯問於子夏曰:“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,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。敢問古樂之如彼,何也?新樂之如此,何也?”
子夏答曰:“今夫古樂,進旅而退旅,和正以廣,弦匏笙簧合守拊鼓,始奏以文,止亂以武,治亂以相,訊疾以雅。君子於是語,於是道古,修身及家,平均天下:此古樂之發也。今夫新樂,進俯退俯,奸聲以淫,溺而不止,及優侏儒,
雜子女,不知父子。樂終不可以語,不可以道古:此新樂之發也。今君之所問者樂也,所好者音也。夫樂之與音,相近而不同。”
文侯曰:“敢問如何?”
子夏答曰:“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,民有德而五穀昌,疾疢不作而無祅祥,此之謂大當。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,紀綱既正,天下大定,天下大定,然後正六律,和五聲,絃歌詩頌,此之謂德音,德音之謂樂。詩曰:‘莫其德音,其德克明,克明克類,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,克順克俾。俾於文王,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,施於孫子。’此之謂也。今君之所好者,其溺音與?”
文侯曰:“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?”
子夏答曰:“鄭音好濫淫志,宋音燕女溺志,衛音趣數煩志,齊音驁闢驕志,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,是以祭祀不用也。詩曰:‘肅雍和鳴,先祖是聽。’夫肅肅,敬也;雍雍,和也。夫敬以和,何事不行?爲人君者,謹其所好惡而已矣。君好之則臣爲之,上行之則民從之。詩曰:‘誘民孔易’,此之謂也。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,此六者,德音之音也。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,干鏚旄狄以舞之。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,所以獻酬酳酢也,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,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。鐘聲鏗,鏗以立號,號以立橫,橫以立武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。石聲硜,硜以立別,別以致死。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。絲聲哀,哀以立廉,廉以立志。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。竹聲濫,濫以立會,會以聚衆。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。鼓鼙之聲讙,讙以立動,動以進衆。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。君子之聽音,非聽其鏗鎗而已也,彼亦有所合之也。”
賓牟賈侍坐於孔子,孔子與之言,及樂,曰:“夫武之備戒之已久,何也?”
答曰:“病不得其衆也。”
“永嘆之,淫液之,何也?”
答曰:“恐不逮事也。”
“發揚蹈厲之已蚤,何也?”
答曰:“及時事也。”
“武坐致右憲左,何也?”
答曰:“非武坐也。”
“聲淫及商,何也?”
答曰:“非武音也。”
子曰:“若非武音,則何音也?”
答曰:“有司失其傳也。如非有司失其傳,則武王之志荒矣。”
子曰:“唯丘之聞諸萇弘,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”
賓牟賈起,免席而請曰:“夫武之備戒之已久,則既聞命矣。敢問遲之遲而又久,何也?”
子曰:“居,吾語汝。夫樂者,象成者也。總幹而山立,武王之事也;發揚蹈厲,太公之志也;武亂皆坐,周召之治也。且夫武,始而北出,再成而滅商,三成而南,四成而南國是疆,五成而分陝,周公左,召公右,六成復綴,以崇天子,夾振之而四伐,盛威於中國也。分夾而進,事蚤濟也。久立於綴,以待諸侯之至也。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?武王克殷反商,未及下車,而封黃帝之後於薊,封帝堯之後於祝,封帝舜之後於陳;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,封殷之後於宋,封王子比干之墓,釋箕子之囚,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。庶民弛政,庶士倍祿。濟河而西,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;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;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複用;倒載干戈,苞之以虎皮;將率之士,使爲諸侯,名之曰‘建櫜’: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散軍而郊射,左射貍首,右射騶虞,而貫革之射息也;裨冕搢笏,而虎賁之士稅劍也;祀乎明堂,而民知孝;朝覲,然後諸侯知所以臣;耕藉,然後諸侯知所以敬:五者天下之大教也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,天子袒而割牲,執醬而饋,執爵而酳,冕而總幹,所以教諸侯之悌也。若此,則周道四達,禮樂交通,則夫武之遲久,不亦宜乎?”
子貢見師乙而問焉,曰:“賜聞聲歌各有宜也,如賜者宜何歌也?”
師乙曰:“乙,賤工也,何足以問所宜。請誦其所聞,而吾子自執焉。寬而靜,柔而正者宜歌頌;廣大而靜,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;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;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;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;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。夫歌者,直己而陳德;動己而天地應焉,四時和焉,星辰理焉,萬物育焉。故商者,五帝之遺聲也,商人志之,故謂之商;齊者,三代之遺聲也,齊人志之,故謂之齊。明乎商之詩者,臨事而屢斷;明乎齊之詩者,見利而讓也。臨事而屢斷,勇也;見利而讓,義也。有勇有義,非歌孰能保此?故歌者,上如抗,下如隊,曲如折,止如木,居中矩,句中鉤,累累乎殷如貫珠。故歌之爲言也,長言之也。說之,故言之;言之不足,故長言之;長言之不足,故嗟嘆之;嗟嘆之不足,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”子貢問樂。
凡音由於人心,天之與人有以相通,如景之象形,響之應聲。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,爲惡者天與之以殃,其自然者也。
故舜彈五絃之琴,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;紂爲朝歌北鄙之音,身死國亡。舜之道何弘也?紂之道何隘也?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,舜樂好之,樂與天地同意,得萬國之驩心,故天下治也。夫朝歌者不時也,北者敗也,鄙者陋也,紂樂好之,與萬國殊心,諸侯不附,百姓不親,天下畔之,故身死國亡。
而衛靈公之時,將之晉,至於濮水之上舍。夜半時聞鼓琴聲,問左右,皆對曰“不聞”。乃召師涓曰:“吾聞鼓琴音,問左右,皆不聞。其狀似鬼神,爲我聽而寫之。”師涓曰:“諾。”因端坐援琴,聽而寫之。明日,曰:“臣得之矣,然未習也,請宿習之。”靈公曰:“可。”因復宿。明日,報曰:“習矣。”即去之晉,見晉平公。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。酒酣,靈公曰:“今者來,聞新聲,請奏之。”平公曰:“可。”即令師涓坐師曠旁,援琴鼓之。未終,師曠撫而止之曰:“此亡國之聲也,不可遂。”平公曰:“何道出?”師曠曰:“師延所作也。與紂爲靡靡之樂,武王伐紂,師延東走,自投濮水之中,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,先聞此聲者國削。”平公曰:“寡人所好者音也,原遂聞之。”師涓鼓而終之。
平公曰:“音無此最悲乎?”師曠曰:“有。”平公曰:“可得聞乎?”師曠曰:“君德義薄,不可以聽之。”平公曰:“寡人所好者音也,原聞之。”師曠不得已,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,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;再奏之,延頸而鳴,舒翼而舞。
平公大喜,起而爲師曠壽。反坐,問曰:“音無此最悲乎?”師曠曰:“有。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,今君德義薄,不足以聽之,聽之將敗。”平公曰:“寡人老矣,所好者音也,原遂聞之。”師曠不得已,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,有白雲從西北起;再奏之,大風至而雨隨之,飛廊瓦,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懼,伏於廊屋之間。晉國大旱,赤地三年。
聽者或吉或兇。夫樂不可妄興也。
太史公曰:夫上古明王舉樂者,非以娛心自樂,快意恣欲,將欲爲治也。正教者皆始於音,音正而行正。故音樂者,所以動盪血脈,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。故宮動脾而和正聖,商動肺而和正義,角動肝而和正仁,徵動心而和正禮,羽動腎而和正智。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;上以事宗廟,下以變化黎庶也。琴長八尺一寸,正度也。弦大者爲宮,而居中央,君也。商張右傍,其餘大小相次,不失其次序,則君臣之位正矣。故聞宮音,使人溫舒而廣大;聞商音,使人方正而好義;聞角音,使人惻隱而愛人;聞徵音,使人樂善而好施;聞羽音,使人整齊而好禮。夫禮由外入,樂自內出。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,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;不可須臾離樂,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。故樂音者,君子之所養義也。夫古者,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,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,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。夫淫佚生於無禮,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,目視威儀之禮,足行恭敬之容,口言仁義之道。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。
樂之所興,在乎防欲。陶心暢志,舞手蹈足。舜曰簫韶,融稱屬續。審音知政,觀風變俗。端如貫珠,清同叩玉。洋洋盈耳,鹹英餘曲。
司馬遷說:我每每閱讀《虞書》,看到君主與大臣相互勸誡、彼此約束,國家才能安定,可一旦大臣不稱職、不忠心,各種事情就會荒廢敗壞,每每讀到此處,都不禁流下眼淚。
古代的音樂,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,不是爲了取悅自己、放縱慾望,而是爲了教化人心、整頓社會秩序。音樂從人心出發,與天地相通,就像影子模仿形體,迴響呼應聲音一樣。做善事的人,上天會以福報相賜;作惡的人,上天會以災禍相加,這是自然的規律。
舜彈奏五絃琴,唱《南風》之詩,天下便太平;商紂王卻喜好朝歌的鄙俗之音,最終身死國亡。爲什麼呢?《南風》是生長萬物的樂聲,能使人內心溫暖,與天地同感,百姓因此歡心,天下得以安定;而紂所喜愛的朝歌之音不正、不時,是敗亡之音,違背天地之理,百姓背離,國家因此崩潰。
古時候的明君制定樂制,根本目的不是爲了自我娛樂,而是要通過音樂來端正人的行爲,使人心正,行爲正。音樂的作用,是調節人的血脈,通暢精神,使內心歸於平和與正直。
宮音能使人內心溫和寬廣,商音使人性格方正有正義感,角音使人產生憐憫心、懂得愛惜他人,徵音使人樂於行善、願意幫助人,羽音使人有條理、重視禮儀。這五種音色,對應人的五種器官與五種德行:宮對應脾,與“聖”相應;商對應肺,與“義”相應;角對應肝,與“仁”相應;徵對應心,與“禮”相應;羽對應腎,與“智”相應。
音樂的起源,在於教化,教化的作用在於防止人的慾望失控。通過音樂陶冶情志,讓人舞動雙足,舒展身心。舜時的《簫韶》樂,讓四方百姓都爲之感動,稱讚其綿延不絕。懂得音樂的人,能從中看出政事的得失,觀察社會風氣的變化。
古代的音樂,如同一串珠子,整齊排列,清朗如擊玉,悅耳動聽,迴響不絕。它不僅能使人內心愉悅,還能讓人從外在舉止中看出德行的高低。
因此,一個國家若要治,必須從音樂開始;音樂正,政事也就正。君王和貴族每天聽鐘磬之聲,大臣每天聽琴瑟之音,都是爲了修養德行、防止放縱。如果一個人失去了禮樂的薰陶,就會產生驕傲、放縱等不良行爲。
所以君子必須時刻不忘禮樂,片刻離開禮樂,就會走上暴戾放縱的道路;片刻離開音樂,內心就會滋生奸邪之念。音樂,是君子養德行、修心性的根本途徑。
古代天子、諸侯在朝廷中聽鐘磬之音,卿大夫在廳堂中聽琴瑟之音,都是爲了修養德行,防止私慾氾濫。慾望一旦失控,就源於缺乏禮制約束,所以聖明的君主讓百姓耳聞《雅》《頌》的正音,目視莊重的禮儀,步伐恭敬,言語仁義。這樣,他們整日說話,邪念邪行都無從進入。
音樂的興起,其根本作用在於節制人的慾望。它能使人心安靜、志向高遠,使人舞動身體,舒展精神。
後來魏文侯問子夏:“我穿上禮服聽古代音樂,總是擔心自己睡着;聽鄭衛之樂,則完全忘了疲倦。請問,爲什麼古代音樂這樣令人專注,而新樂卻令人沉醉?”
子夏回答說:古代的音樂,進退有序,節奏和諧,合於禮制。弦、匏、笙、簧等各種樂器配合鼓點,開始奏樂時文雅莊重,到中間轉爲有力的武樂,以保持秩序,再以雅樂收束,使人內心安定。君子聽了,便開始討論古事,修養自身,推及家庭,最終實現天下太平。這就是古代音樂的教化作用。
而今天的音樂,進退無序,充斥浮淫之音,沉溺不止,甚至雜以優伶、侏儒、女子,毫無父子之序。聽這類音樂,人無法說話,無法談論古事,完全喪失了教化功能。
文侯問:“那這些淫亂的音樂是從何而來的呢?”
子夏說:鄭國的音樂喜好放縱情感,宋國的音樂沉迷於女色,衛國的音樂追求浮華熱鬧,齊國的音樂驕傲張揚,四國的音樂都沉溺於情慾,危害道德,所以祭祀中都不用。
《詩經》說:“肅肅和鳴,先祖聆聽。”“肅肅”是恭敬,“雍雍”是和諧,恭敬與和諧,何事不能成就?爲君者,必須謹慎自己所喜愛和厭惡的事物。因爲君主喜歡什麼,大臣便會效仿;上層如此做,百姓自然跟着學。
所以古代聖人制作了鞉鼓、椌楬、壎、篪等樂器,這些是德音的代表。之後再用鍾、磬、竽、瑟來配合,用干鏚、旄旗、狄舞來舞蹈,這樣纔可用來祭祀祖先,用來行酒禮,用來明確貴賤等級,顯明尊卑長幼的秩序。
鐘聲清亮,用來樹立號令,號令用來樹立武官;聽到鐘聲,人便想到武臣。磬聲沉厚,用來區分身份,區分身份就等於確立生死之義;聽磬聲,人便想到保衛疆土的臣子。
琴瑟之聲哀婉,用來樹立廉正之德,廉正使人立志;聽琴瑟聲,人便想到有德行的臣子。
竽、笙、簫、管之音寬廣,用來聚集衆人;聽這類音樂,人便想到能組織百姓的官員。
鼓、鼙之聲喧鬧,用來激發行動,讓軍隊奮勇前進;聽到鼓聲,人就想到統領軍隊的將領。
君子聽音樂,不只是聽聲音的鏗鏘,更是聽其中的教化意義。
後來賓客牟賈向孔子請教:“《武》這首樂,爲什麼一開始就充滿戒備?爲何反覆感嘆、內心悲痛?爲何動作猛烈、步伐急迫?爲何在座時只坐一邊,不對稱?爲何音調中夾雜了‘商’音?”
孔子說:“如果不是《武》樂,又是什麼樂呢?”
弟子回答:“可能是主管樂官失傳了樂理,如果真是如此,那說明武王的意志已經荒廢了。”
孔子說:“我只聽說萇弘說過這樣的話,和你所說差不多。”
賓客牟賈起身,請求說:“《武》樂一開始就戒備很久,我已經明白了。但爲何要延遲、拖延,又如此長久呢?”
孔子說:“坐下,讓我告訴你。音樂是模仿現實政治的體現。‘總幹而山立’,是武王治國的象徵;‘發揚蹈厲’,是太公姜尚的志向;‘武亂皆坐’,是周公、召公治理時的景象。而且,武王的征戰過程是這樣的:開始向北出征,兩次成功打敗商朝,三次南征,四次鞏固南方疆域,五次劃分疆界,周公在左,召公在右,六次重新集結,鞏固天子權威,兩邊夾擊,四方征伐,彰顯武威。分兵夾擊,可迅速實現目標。長久站立在軍陣之中,是等待諸侯的到來。
更重要的是,你難道沒聽說過牧野之戰的故事嗎?武王攻下商朝,還沒下車,就分封黃帝后代於薊,堯的後代於祝,舜的後代於陳。下車後,分封夏朝後裔於杞,商朝後裔於宋,爲比干埋墓,釋放箕子,讓他重新任職。百姓得以休養生息,士人官職得以恢復。大軍退到黃河以西,馬匹散到華山以南,不再騎乘;牛羣散到桃林以野,不再驅使;戰車兵器收存於府庫,不再使用。將領們把兵器倒置,用虎皮包裹起來;將領們被任命爲諸侯,稱爲‘建櫜’,以表明武王不再用兵。
然後他們散軍舉行郊外射箭活動,左邊射獵野豬,右邊射獵馴鹿,箭射完便休息。穿着隆重服飾,手持笏板,士兵們也放下武器。在明堂祭祀,民衆知道孝道;參加朝會,諸侯知道臣服之道;耕種土地,諸侯知道敬重農事。這五件事,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內容。
在太學中敬拜三老五更,天子袒露上身割肉祭祀,手持醬器供奉,飲酒時執爵祝酒,穿戴禮服,手執橫木,以此教育諸侯懂得兄弟和睦的美德。
像這樣,周朝的政令暢通,禮樂互通,所以《武》樂的緩慢與長久,也合乎情理了。”
子貢見師乙,問:“我聽說,不同的音樂適合不同的人。我應當唱哪一類音樂?”
師乙說:“我是地位低下的樂工,哪有資格回答你。我只敢把你聽過的音樂講出來,你自行判斷。性格寬厚、安靜、溫和正直的人適合唱《頌》;心胸宏大、沉穩、通達信任的人適合唱《大雅》;恭敬節儉、喜愛禮節的人適合唱《小雅》;正直清廉、謙虛謹慎的人適合唱《風》;直接坦率、慈愛寬容的人適合唱《商》;溫和仁厚、能決斷的人適合唱《齊》。
唱歌,是直抒胸臆、表達德行;人的內心一動,天地就會相應,四季就協調,星辰運行也有序,萬物生長就順利。《商》是五帝遺留下來的樂聲,商人喜歡它,所以叫商;《齊》是三代流傳下來的樂聲,齊國人喜歡它,所以叫齊。明白《商》樂的人,遇到事情就能果斷決斷;明白《齊》樂的人,見到利益時便能謙讓。果斷決斷是勇氣的體現,謙讓是仁義的表現。有勇氣有仁義,除了唱歌,還能依靠什麼來保全呢?
唱歌時,音調要如高山之屹立,如江河之奔流,如彎曲的樹木,要舒緩平穩,如停止時的樹樁,居中要端正,轉折要圓潤,如同一串串珍珠,連貫而有節奏。所以‘歌’,是長篇的表達。因爲話語不足,所以要延長表達;表達仍不足,所以要嘆息;嘆息仍不足,所以就忍不住手舞足蹈。
凡是音樂都產生於人心。天地與人之間,有着相通的感應,就像影子模仿形體,回聲回應聲音。所以行善的人,上天以福報回報;作惡的人,上天以災禍懲罰,這都是自然的法則。
舜彈五絃琴,唱《南風》之詩,天下便大治;紂王喜歡朝歌的鄙俗之音,最終身死國亡。舜的教化何等寬廣?紂的道行何其狹隘?《南風》是生長萬物的樂,舜喜歡它,與天地心意相通,能獲得萬民的擁戴,所以天下太平;朝歌之音是不合時宜的,北是敗亡之象,鄙是卑陋之音,紂王喜愛它,與天下人心背離,諸侯不歸附,百姓不親和,天下因此叛亂,最終身死國亡。
到了衛靈公時期,他將要去晉國,途經濮水,半夜聽見鼓琴聲。他問左右,都說聽不到。於是召來師涓說:“我聽見有人在彈琴,問左右,都說沒有聽到。那聲音像鬼神一樣,來爲我記下來。”師涓說:“好。”於是端坐撫琴,用心聽並記錄了下來。第二天,他說:“我記下了,但還沒熟練,想留宿練習。”靈公同意了。第二天,師涓說:“我已經熟練了。”就去了晉國,拜見晉平公。
晉平公在施惠臺設宴,酒興正濃,衛靈公說:“我今天聽到新樂,請演奏一下。”平公說:“可以。”他命師涓坐到師曠旁邊,彈奏起來。樂曲未終,師曠便用手一攔說:“這是亡國之音,不能繼續演奏!”平公問:“爲什麼?”
師曠說:“這是師延所作的樂曲。師延曾與商紂王一同創作靡靡之音,武王伐紂時,師延向東逃亡,投奔濮水而死。所以只有在濮水附近,才能聽到這聲音,最早聽到的人國家必定衰敗。”
平公說:“我只喜歡音樂,想繼續聽。”師涓於是彈奏到底。
平公問:“這樂曲難道是最悲傷的嗎?”師曠說:“有。”平公說:“可以讓我聽一聽嗎?”
師曠說:“您的德行和道義淺薄,不適合聽這種樂曲,聽了會招致災禍。”平公說:“我只喜歡音樂,想聽。”師曠無奈,只好拿起琴彈奏。
第一奏,兩隻玄鶴聚集在廳堂門前;第二奏,鶴伸長脖子鳴叫,張開翅膀起舞。
平公非常高興,起身敬祝師曠。回來後問:“這樂曲是不是最悲傷?”師曠說:“是的。從前黃帝用音樂調和鬼神,如今您的德行淺薄,不足以聽這種音樂,聽它會帶來失敗。”
平公說:“我已經老了,只喜歡音樂,想聽。”師曠無奈,再次彈奏。
第一奏,有白雲從西北方向升起;第二奏,大風驟起,大雨隨風而來,吹飛了屋瓦,左右賓客紛紛逃竄。平公嚇壞了,躲進屋內。晉國三年大旱,土地乾裂。
由此可見,聆聽音樂,可能帶來福,也可能帶來禍。音樂絕不可隨意興起。
司馬遷最終說:上古的聖明君王制定音樂,並不是爲了自我享樂,也不是爲了放縱慾望,而是爲了實現治理天下、教化萬民的目的。教化始於音樂,音樂正,行爲才正。音樂的作用,是使血脈暢通,精神振奮,內心平和正直。
宮音調和脾,使人溫順寬和,象徵“聖”;商音調和肺,使人方正有義,象徵“義”;角音調和肝,使人有憐憫之心,象徵“仁”;徵音調和心,使人樂於行善,象徵“禮”;羽音調和腎,使人有條理,象徵“智”。
所以音樂是內裏修養正心、外在區別貴賤的工具。上層用於祭祀宗廟,下層用於感化百姓。
古琴長八尺一寸,是合乎標準的尺寸。弦中最大者定爲宮音,居於中央,代表君主;其餘弦在右側,大小依次排列,不越次序,就等於君臣地位的明確與端正。
聽到宮音,人會變得溫和寬廣;聽到商音,人會變得方正講義;聽到角音,人會變得有同情心,懂得愛人;聽到徵音,人會變得樂於行善、樂於施捨;聽到羽音,人會變得整齊有禮。
禮是外在表現,樂是內在修養。所以君子一刻也不能離開禮,離開禮,就會產生暴戾放縱的行爲;一刻也不能離開音樂,離開音樂,內在的奸邪之念就會滋生。
因此,音樂是君子修養德行的根本。古代的天子、諸侯,每天在朝廷聽鐘磬之音;卿大夫在廳堂聽琴瑟之音,都是爲了修養品行,防止放縱。
慾望若無禮制約束,就會氾濫。所以聖明的君主讓百姓耳聞《雅》《頌》的正音,目視威嚴的禮節,腳步恭敬,言語符合仁義。因此,君子整天說話,邪妄之念無處可入。
音樂的興起,其根本目的是防止人的慾望膨脹。它使人心舒暢、志向堅定,讓人手舞足蹈,盡情舒展。
舜時的《簫韶》,被世人稱爲“動天地、感萬民”,稱其“綿延不絕,餘音繞樑”。懂得音樂的人,能從中察覺政事的得失,觀察社會風氣的變遷。音樂如珠串般有序、清亮如擊玉,響徹耳中,餘音不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