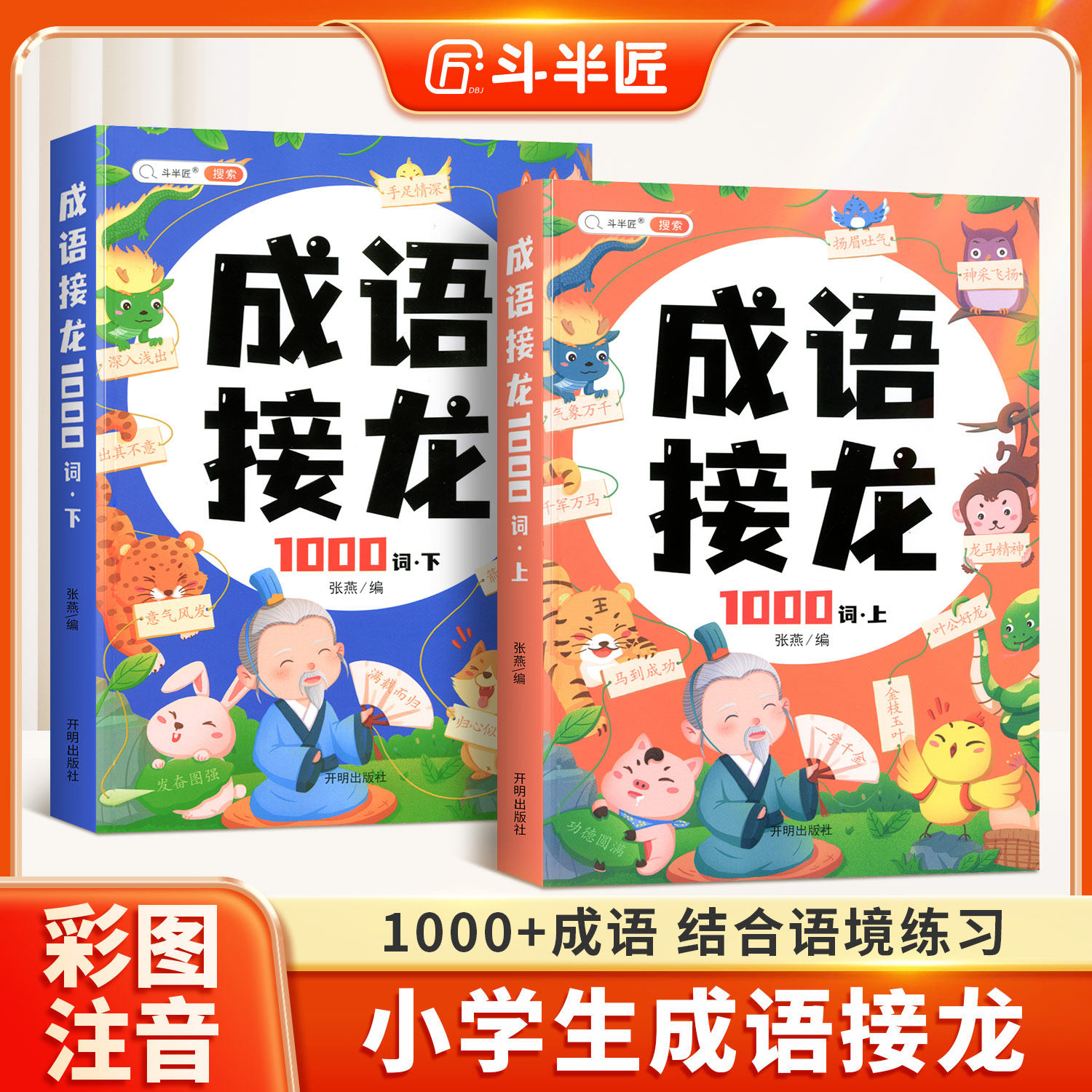卜葬得假告,南出安上门。 鞭马六十里,暮投中书村。 村翁馆我宿,茅屋欲黄昏。 有客忽投刺,自称一品孙。 气貌不凡俗,因为开酒樽。 坐久问家谍,其族大且繁。 池州有清节,滥觞登洪源。 太傅擅鸿笔,入相又出藩。 其家本开封,改号一何尊。 至昱始六代,布衣老丘樊。 跨馿入府县,驱犊耕郊原。 家庙固已毁,国史空具存。 盛德百世著,功必格乾坤。 高太已不祀,羡𬘡何可论。 况复起章句,乘时宠便蕃。 子孙虽替陵,尚得守田园。 我爱三代时,法度有深根。 卿大夫称家,世世奉苹蘩。 四民有定分,宦路无驰奔。 自从杂伯道,倾夺日喧喧。 脱耒秉金钺,吮笔乘朱轩。 朝荣又暮辱,容易如掌翻。 古道不可复,颓波益以浑。 何况度木者,倒置轮与辕。 我亦起白屋,两朝直紫垣。 荫子有官常,赏延弟与昆。 尽待食人禄,将何报君恩。 农桑国之本,孝义古所敦。 吾族不力穑,终岁饱且温。 虽非享富贵,亦以蠹黎元。 唐贤尚消歇,我辈奚足言。 呼儿讽此诗,播在篪与埙。
一品孙郑昱
译文:
我因为要为亲人选择墓地获得了假期,从南边的安上门出城。
策马奔驰六十里路,傍晚时分投宿到中书村。
村里的老翁安排我住宿,那简陋的茅屋在黄昏的暮色中显得愈发昏暗。
这时有位客人忽然递上名帖,自称是一品大员的子孙。
他气质容貌不同凡俗,于是我便打开酒樽与他共饮。
坐了许久我询问他家的族谱,才知道他的家族庞大又繁盛。
他们家族从池州那位有清廉节操的先人开始,就像涓涓细流汇聚成宏大的洪流之源。
太傅大人擅长写作,既能入朝为相又能出京治理藩地。
他家原本是开封的名门,名号更改后更是尊贵。
到孙郑昱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,却只是个在乡野终老的平民。
他骑着驴子往来于府县之间,赶着牛犊在郊外的原野上耕种。
家族的宗庙早已毁坏,只有国史中还留存着他们家族的记载。
先人的大德流传百世,功勋必定能感动天地。
高祖、太祖这些祖先都无人祭祀了,那些祭祀时的美好氛围更不必说了。
更何况如今靠文章科举兴起,当时的恩宠十分繁多。
子孙虽然已经衰落,但还能守住田园。
我怀念夏商周三代的时候,那时的法度根基深厚。
卿大夫有自己的家族,世世代代供奉着祭祀用的苹蘩。
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固定的名分,仕途上没有追名逐利的乱象。
自从夹杂了霸道的治国之道,倾轧争夺之事日益喧闹。
有人放下农具拿起兵器,有人放下笔杆乘坐华丽的马车。
早上还荣耀加身傍晚就遭受屈辱,变化就像手掌翻转一样容易。
古代的正道难以恢复,这颓败的世风愈发浑浊。
更何况那些用人的人,就像做木工活却把车轮和车辕安反了一样。
我也是出身贫寒之家,在两朝都在朝廷中任职。
子孙凭借我的恩荫获得官职,赏赐还惠及兄弟。
大家都等着享受朝廷的俸禄,拿什么来报答君主的恩情呢?
农业和桑蚕业是国家的根本,孝顺仁义是古人所推崇的。
我的族人不努力耕种,却能终年衣食温饱。
虽然没有享受大富大贵,但也算是损害百姓的蠹虫了。
唐代的贤能之士都已消逝,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?
我呼唤儿子诵读这首诗,让它像篪和埙的声音一样传播开来。
纳兰青云